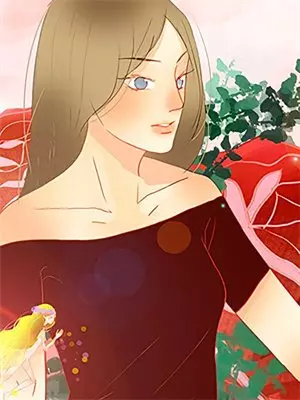
我花了五年时间,把沈念从一个骄傲的芭蕾舞者,变成了一个唯唯诺诺的家庭主妇。
我羞辱她的梦想,打压她的自尊,让她相信除了我,她一无是处。她生日那天,
我故意当着她的面搂着新欢进门:“穿好你的围裙,别出来丢人。
”她只是沉默地把炖了八个小时的汤倒进垃圾桶,然后消失在厨房里。后来,
我在国际芭蕾舞团的新闻发布会上看到她。记者问她成功的秘诀是什么。
她对着镜头微微一笑:“感谢一位先生,他用五年的时间告诉我,离开他,我什么都能做成。
”第一章 驯服我第一次见到沈念,是在市歌剧院的舞台上。那年她二十二岁,
是舞蹈团最年轻的独舞演员,跳《天鹅湖》里的白天鹅奥杰塔。我坐在VIP席第三排,
原本是陪客户来的,对这种高雅艺术没什么兴趣,低着头回邮件。幕布拉开,音乐响起,
我鬼使神差地抬了抬头。聚光灯打在她身上,白色的纱裙轻盈得像一团雾,她踮着脚尖旋转,
手臂柔软地起伏,像一只真正的天鹅在湖面上游弋。我看呆了,手机屏幕暗了都没发现。
谢幕的时候,她站在舞台中央鞠躬,汗湿的碎发贴在额头上,脸颊红扑扑的,眼睛亮得惊人。
她抬起头,正好看向VIP席的方向,我们的目光在空中撞了一下。就那一下。
我让人去打听她。三天后,她的资料就放在了我的办公桌上。沈念,二十二岁,
父母都是普通工人,六岁开始学芭蕾,十八岁考入市歌舞团,二十岁成为独舞演员。
没有背景,没有靠山,只有一双磨破了无数次又重新结痂的脚。追求她并不难。我这样的人,
见惯了名利场上的虚与委蛇,知道怎么打动一个单纯的姑娘。送花,包场看她演出,
在她排练到深夜的时候开车等在门口,说是顺路。她拒绝了很多次。每一次都红着脸,
眼神躲闪,说陆总您别这样,我们不合适。我问她哪里不合适。她说,您一看就是有钱人,
我配不上。我笑了。这姑娘真傻,不知道自己有多好看。追了三个月,
她才终于答应跟我吃顿饭。那天她穿了一条鹅黄色的连衣裙,头发披散下来,
比舞台上还要好看。我盯着她看了很久,心里想的不是她多美,而是——这么干净的人,
要是弄脏了,会是什么样子?这个念头只闪了一下,就被我按了下去。在一起之后,
我开始一点点改变她。先是穿着。“这条裙子太短了,穿出去不安全。
”我把她刚买的裙子扔到一边,“我给你买几条长裙。”她有点委屈:“可是我喜欢这条。
”“听话。”她看了看我的脸色,没再坚持。然后是社交。“那些跳舞的朋友,以后少来往。
”我说,“他们那个圈子乱,我不放心。
”她犹豫:“他们都是很好的人……”“你是不信我?”她摇头,
从此和舞团的朋友渐渐断了联系。最难的是芭蕾。我知道跳舞对她意味着什么。她说过,
九岁那年第一次踮起脚尖的时候,她就知道自己这辈子要做这件事。跳舞的时候,
她才觉得自己是活着的。可我就是想让她放弃。说不清为什么。
也许是嫉妒——她在舞台上发光的样子,
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偷窥者;也许是因为不安——这样的她太耀眼了,迟早会被别人抢走。
“芭蕾舞能跳一辈子?”我第一次提这件事的时候,语气很温和,“现在不转行,
以后年纪大了怎么办?”她愣了一下,说:“我可以当老师。”“教别人跳舞?能挣几个钱?
”她低下头,没说话。那天晚上,她抱着我,小声问:“你是不是不喜欢我跳舞?
”我没回答。之后每次她提起排练的事,我都表现得很不耐烦。渐渐的,她不再提了。
有一天回家,我看见她在阳台上烧什么东西。走近一看,是一双舞鞋。火焰舔舐着缎面,
粉色的鞋带卷曲起来,化成灰烬。她盯着那团火,脸上没什么表情。“烧了干什么?”我问。
她转过头看我,眼眶有点红,却笑了一下:“用不着了,放着也是占地方。
”我把她搂进怀里,心想,这姑娘终于学乖了。同居第二年,她彻底搬进了我的公寓。
那套公寓是我爸妈留给我的,一百四十平,装修是冷硬的黑白灰风格。她搬进来之后,
客厅的茶几上多了一盆绿萝,餐桌上多了块碎花桌布,浴室里摆满了瓶瓶罐罐。我没有反对。
这些东西无伤大雅,还能让她有种“家”的错觉。她没有工作,我给了她一张副卡,
每个月额度五万。她花得不多,最多就是买点菜、买点日用品,偶尔给自己买条裙子。
每次刷完卡,她都会把账单拿给我看,小心翼翼地说今天买了什么,花了多少。
有一次我说:“不用给我看。”她说:“我怕你嫌我乱花钱。”我看着她,忽然有点不舒服。
不是因为她乱花钱,而是因为——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卑微了?我让她出去找工作,
不是为了钱,就是单纯想找点茬。她找了半个月,拿回来一堆面试邀请。我挨个看过去,
说这个公司不行,那个行业不好,这个离家太远,那个加班太多。最后她放弃了。
那天晚上她做饭,切菜切到了手指。我帮她包扎,她低着头,忽然说:“陆时晏,
我是不是很没用?”我包扎的动作顿了顿。“不会赚钱,也不会应酬,除了跳舞什么都不会。
可是舞也不让我跳了……”她的声音越来越低。我捏着她的手指,心想要不要安慰她几句。
可我什么都没说。同居第三年,我爸妈来家里吃饭。那顿饭沈念准备了两天,
菜单反复改了四五遍。红烧肉、清蒸鲈鱼、蒜蓉青菜,每一道都是我爸妈爱吃的家常菜。
饭桌上,我妈夹了一筷子鱼,嚼了嚼,皱起眉头:“这鱼蒸老了。”沈念筷子一顿,
小声说:“阿姨,我下次注意。”“下次?”我妈放下筷子,“听说你现在没工作?
天天在家就做这些?”沈念低着头,脸涨得通红。我爸在旁边咳了一声:“行了,吃饭。
”我妈不依不饶:“小念啊,阿姨说这些话是为你好。我们家时晏条件好,
追他的姑娘多得很。你现在不工作,不赚钱,以后怎么办?靠他养一辈子?男人是会变的。
”我靠在椅背上,一句话都没说。沈念抬起头看了我一眼,那眼神里有委屈,有求助,
还有一点点——期盼。我假装没看见。那天晚上送走我爸妈,沈念在厨房刷碗,刷了很久。
我过去看了一眼,她对着水槽发呆,水流哗哗地响,手泡在冷水里已经发白了。“愣着干嘛?
”我问。她回过神,关掉水龙头,擦了擦手。“陆时晏,”她背对着我,声音闷闷的,
“你妈说的那些话,你也这么想吗?”“我妈就那样,别往心里去。”“可是你什么都没说。
”她转过身,眼睛红红的,“你就在旁边看着。”我皱起眉:“你想让我说什么?
跟她吵一架?”她张了张嘴,最终什么都没说,低下头继续刷碗。那天晚上她背对着我睡,
一夜没翻身。凌晨的时候,我迷迷糊糊听见她在哭,哭得很压抑,肩膀一抖一抖的。
我翻了个身,假装没听见。同居第四年,她爸妈来市里看病,想见见我。
沈念提前半个月就跟我说了这件事,每天小心翼翼地问我想吃什么,到时候怎么安排。
我说随便,她就一脸忐忑地继续安排。见面的那天,我迟到了一个小时。到了饭店,
沈念和她爸妈已经等了很久。她妈脸色不太好,她爸一个劲地抽烟。沈念站起来迎我,
笑着问路上是不是堵车。“嗯。”我把车钥匙扔在桌上。饭吃到一半,
沈念她爸开口了:“小陆,你们在一起也四年了,什么时候考虑结婚的事?
”我放下筷子:“不急。”她爸脸色变了变:“小念年纪不小了……”“我说了不急。
”我打断他。沈念在旁边拼命打圆场,说我们还年轻,想多奋斗几年。她妈心疼地看着她,
眼圈都红了。那天吃完饭,我借口公司有事,先走了。后来沈念告诉我,
她爸回去就病了一场,气得。她妈哭着说,闺女,你怎么就找了个这样的人?
我问她:“你怎么回的?”她沉默了很久,说:“我说你对我很好。”我笑了,
伸手捏她的脸:“撒谎。”她没躲,就那样看着我,眼神里有什么东西碎了。同居第五年,
沈念变了一个人。她不再跟我吵架,不再提跳舞的事,不再穿亮色的衣服,
不再跟以前的朋友联系。每天早起给我做早饭,晚上等我回家,无论多晚都等。我发脾气,
她低着头听;我带别的女人回家,她躲进厨房不出来。有一次我喝多了,
指着她说:“你知道你像什么吗?像一条狗。”她没说话,低头给我盛醒酒汤。
那碗汤递到我手边,热气氤氲中,我看见她的手指微微发抖。就是那个瞬间,
我心里忽然升起一种奇怪的满足感。看,我把一个骄傲的芭蕾舞者,
变成了一个唯唯诺诺的家庭主妇。她不会再飞走了,她哪里都去不了。我从来没想过,
一个人沉默,不是因为认命,而是在攒离开的勇气。第二章 雪崩出事那天是沈念的生日。
我知道是她生日。早上出门的时候,她站在门口送我,小心翼翼地说:“晚上早点回来,
我炖了你爱喝的排骨汤。”我“嗯”了一声,上了车。后视镜里,她还站在门口,
穿着那件灰扑扑的家居服,目送我的车拐出小区。已经是十一月了,风很大,
吹得她头发乱飞。林鸢鸢的电话在中午打进来。“陆总,晚上有空吗?我朋友开了家新会所,
想请您赏光。”我靠在办公椅上,转了转手里的笔:“几点?”“八点,可以吗?
”我想了想,沈念那锅汤大概七点炖好。“八点,我去接你。”挂了电话,我继续看文件,
一下午什么都没看进去。脑子里总闪过沈念早上站在门口的样子,
还有她那句话——“我炖了你爱喝的排骨汤。”我爱喝吗?我根本不爱喝。我说过很多次,
不喜欢汤里放红枣,太甜了。可她每次都放,说补气血,说我工作太累,该补补。真是烦。
七点半,我开车去接林鸢鸢。她今天穿了一条红裙子,画了精致的妆,
一上车就凑过来问:“陆总,我今天好看吗?”我敷衍地点点头。路过花店的时候,
她非要下车买花。我坐在车里等,看见橱窗里摆着一束白色的玫瑰,
忽然想起沈念以前也喜欢花。她最喜欢的是铃兰,说那花像一串小铃铛,风一吹好像在响。
后来她不买了,因为我说那花放家里招虫子。林鸢鸢抱着一大束红玫瑰上车,
在我脸上亲了一口:“走吧,陆总。”八点半,我搂着林鸢鸢进了家门。门推开的时候,
我看见沈念站在餐桌边,正在往汤碗里盛汤。听见门响,她抬起头,
脸上的笑还没来得及展开,就僵在了那里。她看着我,看着林鸢鸢,看着我搂着林鸢鸢的手。
林鸢鸢往我怀里缩了缩,娇滴滴地说:“陆总,这是你家啊?”我没理她,看着沈念。
沈念穿着那件灰扑扑的家居服,围着一条沾了油渍的围裙,手里还端着汤碗。
灯光照在她脸上,她老了好多,皮肤蜡黄,眼睛下面青紫一片,头发随便扎着,
碎发散落下来,乱糟糟的。这是我的女朋友吗?还是我家的保姆?她站在那里,
像一株枯萎的植物。“愣着干嘛?”我皱了皱眉,“穿好你的围裙,别出来丢人。”她没动,
只是看着我。那目光让我有点不舒服。不是愤怒,不是委屈,甚至不是伤心。
是一种很平静的、我从未见过的目光。“我说的话没听见?”我提高声音。
她低头看了看手里的汤碗,又看了看餐桌——餐桌上摆着四菜一汤,都是我爱吃的,
还点着蜡烛,旁边放着一束花,是她自己用彩纸折的玫瑰。她放下汤碗,慢慢摘掉围裙,
叠好,放在椅背上。然后她端起汤碗,走向厨房。“沈念。”我喊她。她没回头。
我听见厨房门关上的声音,然后是哗哗的水声。过了一会儿,水声停了,有脚步声,
厨房门开了又关上。她回到客厅,摘掉那束彩纸玫瑰上的小卡片,放进围裙口袋里,
然后把花扔进了垃圾桶。做完这些,她看着我,很轻地问了一句:“陆时晏,
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?”“你生日。”我说,“明天补给你。”她笑了。
那笑容让我后背发凉。“不用了。”她说,“你不用补我什么。”她转身上楼,脚步声很轻,
像怕惊动什么似的。林鸢鸢在旁边扯我的袖子:“陆总,她是谁啊?”“没谁。
”我搂着她往客厅走,“看电视吗?”那天晚上我喝了不少酒,
林鸢鸢什么时候走的我都不知道。半夜醒来,躺在沙发上,头疼得厉害。客厅里黑漆漆的,
只有窗外透进来一点光。我忽然想起那锅汤。走到厨房,打开灯,
垃圾桶里飘出红枣的甜腥味。汤全倒了,排骨和红枣混在一起,泡在脏水里。我站了很久。
第二天醒来,已经下午两点了。家里很安静。我喊了一声“沈念”,没人应。上楼一看,
卧室的门开着,床铺得整整齐齐,衣柜里少了她的几件衣服,
洗手台上她的牙刷和护肤品不见了。我走下楼,
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两把钥匙——一把是门钥匙,一把是车钥匙,我那辆偶尔让她开的旧奥迪。
钥匙下面压着一张纸,纸上只有一行字:“汤我倒了,以后不用再炖了。”没有署名,
没有日期,没有任何多余的话。我拿着那张纸,站在客厅里,阳光从窗户照进来,
刺得眼睛疼。她真的走了。我坐进沙发里,拨通了她的电话。关机。再拨,还是关机。
放下手机,我看着茶几上那两把钥匙,忽然想起来——她没带走那张副卡。
她的东西收拾得很干净。洗手台上的护肤品瓶子都空了,应该是早就用完的。衣帽间里,
她的衣服还挂着不少,都是这几年我给她买的那些灰扑扑的衣服。
她自己买的那些鹅黄色、浅蓝色的裙子,一件都没了。卧室的床头柜上,
放着一个用旧了的丝绒盒子。我打开,里面是一双小小的舞鞋——不是真鞋,是个钥匙扣,
应该是很多年前买的,缎面已经磨得起毛了。我把它扔进了抽屉里。那天晚上,我出去喝酒。
林鸢鸢打了好几个电话,我一个都没接。坐在酒吧里,
我一遍遍想起沈念站在门口目送我离开的样子,想起她摘掉围裙时的平静,
想起她说“汤我倒了,以后不用再炖了”。她说得那么轻,像是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。
酒吧打烊的时候,我拿出手机,又拨了一次她的电话。还是关机。第二天我让人去她老家找。
她爸妈说,没见女儿回来。去舞团问。以前的朋友说,好几年没联系了。
去她可能去的任何地方。都没有。沈念像是人间蒸发了。林鸢鸢问我是不是在找什么人。
我说没有。我妈打电话来,问沈念怎么不接电话。我说分了。我妈说,分了好,
那姑娘配不上你。我没说话。就这样过了三个月。三个月里,我每天早上起床,
习惯性地等早餐。厨房里空空的,灶台冰凉。晚上回家,客厅黑漆漆的,没有人等我,
没有热汤。有一次我半夜胃疼,想喝点热水,自己烧了半天没烧开,最后灌了一瓶矿泉水,
躺在沙发上疼到天亮。沈念在的时候,每天晚上都会给我热一杯牛奶。我说不喝,
她第二天还是照热。那时候不觉得有什么。现在想喝,没人给热了。那天下午,
我去机场接一个客户。车开到机场高速,堵车,百无聊赖地往窗外看。
地铁站的大屏上在放广告,一个接一个,卖房的、卖车的、旅游的。然后我看见了她。
屏幕上,她穿着白天鹅的舞裙,站在聚光灯下,手臂舒展,脚尖点地,
整个人像一只正要起飞的鸟。镜头拉近,她对着镜头笑,那笑容明媚得像春天的太阳。
广告词从屏幕下方滑过:国际芭蕾舞团首席舞者沈念,全球巡演荣耀归来。
我的手机差点从手里滑下去。后面的车在按喇叭,我没听见。我就那样盯着大屏,
盯着她的脸,盯着屏幕上那几个字。国际芭蕾舞团首席舞者。三个月。三个月前,
她还是一个穿着灰扑扑家居服、给我炖排骨汤的家庭主妇。三个月后,
她成了国际舞团的首席。这三个月,发生了什么?晚上回家,我打开电脑,搜她的名字。
网页跳出来,全是新闻。“天才舞者沈念阔别五年惊艳复出,
三个月拿下首席之位”“专访沈念:离开舞台的五年,
我经历了什么”“国际舞团总监盛赞沈念:她是我见过最有韧性的舞者”我一篇篇点开看。
有一篇采访里,记者问她,离开舞台这五年在做什么。她说:“在一个地方待着。
”记者问:“什么地方?”她笑了笑,说:“一个不适合我的地方。”还有一篇,记者问她,
这五年有没有想过放弃跳舞。她说:“每天都会想。早上醒来想,晚上睡觉想。
后来就不想了。”“为什么?”“因为想也没用。”记者追问:“是因为现实条件不允许吗?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