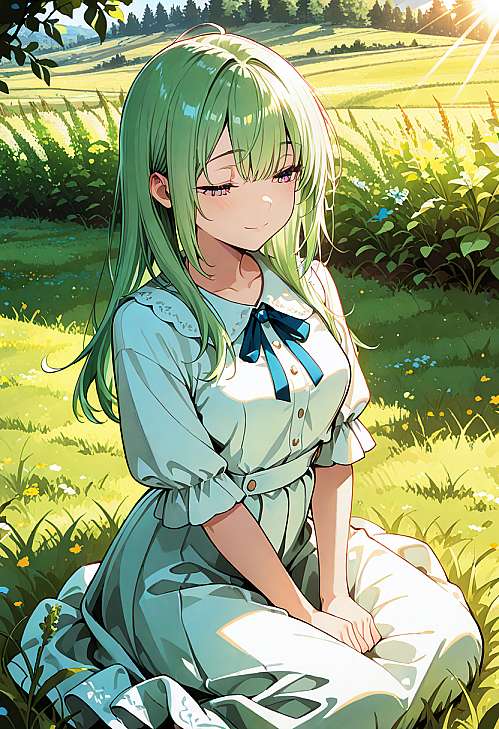# 第一章:血诏·性转·佞臣路雪是灰的。陆清棠的指甲嵌进雪里,血顺着指缝渗出来,
融开一小片暗红。她刻第一个字:陆。父亲的名字。刀落下的时候,父亲没有喊。
他只是看着她,嘴唇动了一下,像在说:记。头颅滚进雪堆,血喷得很高,溅到她脸上。
温的。她刻第二个字:林。母亲的名字。母亲撞向刑柱前,朝她摇头——不要哭。
血从额角流下来,在雪地上蜿蜒成一条细蛇。她继续刻。十六个名字。
祖父、祖母、大伯、堂兄、乳母、管家……血不够用了,她就用指甲刮,刮到指甲翻开,
露出粉色的肉。雪渗进伤口,疼得发麻,这麻让她清醒。第十六个名字刻完,
刽子手的影子笼罩下来。刀锋的冷气先一步贴上后颈。她最后刻了一个字:恨。
笔划刚拖到一半,刀风劈下——无数声音涌进耳朵。不是耳朵,是直接灌进脑髓里的碎响。
像一百个人同时低语,又像隔着水听庙里的钟。
“直谏之志……未绝……”“绑定……”“条件……”眼前炸开白光。白光里,
她看见自己坐在史馆里,烛火摇晃。手里握着一支笔,笔尖悬在纸上。
纸上的标题是:《戾帝本纪·萧彻》。笔落下,墨迹晕开——幻象碎了。雪又回来了,
刀还悬在头顶,但停住了。刽子手一动不动,像尊泥塑。周围的一切都凝固了,
连飘雪都停在半空。眼前浮起几行字,不是看见的,
是直接刻进意识里的:死谏证道系统绑定成功主线任务:完成史上最轰动死谏,
限:三年前置条件:①性转为男性 ②成为萧彻最信任的佞臣失败惩罚:魂飞魄散,
陆家彻底湮灭于历史陆清棠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。她想笑,笑不出来。“若我不从?
”那些碎响安静了一瞬。然后她看见了:陆家的废墟。不是现在的废墟,是几年后的。
断墙长满青苔,野草高过腰,乌鸦在梁上做窝。没有墓碑,没有祭品,
连路过的人都会绕开走。一块残破的木牌半埋在土里,隐约能辨出一个“陆”字。风吹过,
木牌倒了。她懂了。“我接受。”声音哑得像磨砂,“但有个条件。”“让我记住所有的痛。
”“陆清棠的记忆,陆清棠的身体感受,一样都不许少。”“我要带着这些,去杀他。
”碎响又涌上来,这次带着某种冰冷的赞许。
条件追加:保留宿主全部记忆及痛觉感知性转程序启动剧痛是从骨头里开始的。
像有无数根针在骨髓里搅,把什么东西拆开,又拼成另一种形状。她蜷缩在雪地里,
牙齿咬破了嘴唇。血滴在雪上,和父亲的血混在一起。身体在拉长,肩变宽,喉结凸出来。
胸前束紧的压迫感消失了,取而代之的是陌生的平坦。痛。不止是骨头,还有皮肤。
每一寸都在撕裂重组。她看见自己的手——指节变粗,青筋凸起,指甲缝里还嵌着雪和血。
最后一道痛是嗓子。有什么东西在喉咙里烧,声带绷紧、变厚。她想喊,
发出的却是嘶哑的、介于少年和青年之间的声音。痛停了。雪又开始飘。刽子手动了一下,
刀继续落下——砍在空地上。陆清棠已经滚到一边。
她——他现在是“他”了——撑着雪地站起来,腿在抖。新身体太高,重心不稳。
“鬼……鬼啊!”刽子手丢了刀,连滚爬爬跑开。刑场空荡荡的。十七具尸体横在雪里,
血把雪地染成泼墨画。他跪下来,一个一个合上他们的眼睛。合到母亲时,他停住了。
母亲的眼睛睁着,瞳孔里映着灰白的天。他伸手去抚,指尖碰到睫毛的瞬间,
母亲的眼角落下一滴泪。冻住了,凝在脸颊上,像颗冰珠子。他抠下那滴泪,握在手心。
冰渣刺进掌纹。“等我。”***三天后,陆家废墟。新身体很虚弱。走三步喘一口,
喉咙里总有股铁锈味。他在倒塌的书房前站了很久,想搬开压着书架的石柱。石柱纹丝不动。
他喘着气坐下,雪水浸透单薄的衣裤。父亲的话突然撞进脑子里:“清棠,
史家之力不在筋骨,在眼与心。”眼与心。他重新打量这堆废墟。
书架倒下的角度很奇怪——不是被砸倒的,是朝某个方向倾斜。他爬过去,
顺着书架指的方向看。墙根处有道裂缝,被碎瓦半掩着。手伸进去,摸到油布包。三样东西。
半截玉簪。羊脂白玉,簪头雕着细密的缠枝莲——林家的家徽。断口很新,
像是被硬生生掰断的。一张血书残页。父亲的笔迹,墨里掺了血,
字迹潦草:“……猎场……帝袖藏毒箭……弑兄……”最后是一封密信。母亲的字,
娟秀工整:“若事败,寻宫人翠姑,西六所洒扫婢女,曾为林婉贴身侍女。可信。
”他把三样东西贴肉藏好。身上的衣服是捡的,粗麻布,洗得发白。他走到当铺门口,
犹豫了一下,还是进去了。掌柜撩起眼皮:“死当活当?”“死当。”衣服摊在柜台上,
袖口有补丁,领子磨破了。掌柜捏了捏布料:“五十文。”“这是苏锦。”“洗糟了。
”掌柜敲算盘,“六十文,最多。”他沉默片刻,从怀里摸出那半截玉簪:“这个呢?
”掌柜的眼睛亮了。接过玉簪,对着光看,指尖摩挲簪头的缠枝莲。“哪来的?”“家传。
”“死当?”“活当。”他说,“三个月后我来赎。”掌柜盯着他看了很久。少年瘦得厉害,
脸色苍白,但眼睛很亮,亮得让人不舒服。“十两。”掌柜说,“三个月不赎,东西归我。
”“成交。”银子揣进怀里,沉甸甸的。他走到巷口,买了两个馒头,蹲在墙角吃。
馒头冷硬,噎得喉咙发疼。他慢慢嚼,脑子里盘算。十两银子。A:买药,租间小屋,
把身体养好。稳妥,但慢。三个月时间太奢侈。B:全部拿去打通翠姑的门路。赌。
他咽下最后一口馒头,站起来,朝皇宫西边的杂役巷走去。***翠姑的干儿子叫福顺,
十六七岁,在御膳房打杂。约见的地方是护城河边的柳树下,夜黑风大。福顺缩着脖子,
眼睛滴溜溜转:“你真姓林?
”沈清辞——他给自己取的名字——从怀里掏出玉簪:“我母亲是林婉表姐。林家败落得早,
母亲嫁到陆家后,和婉姨还有往来。”福顺凑近看玉簪,手指在缠枝莲上摸了摸。
“林婉姑娘……”他压低声音,“宫里不许提这个名字。陛下会发疯。”“我不问旧事。
”沈清辞说,“只问现在:陛下最近常去何处?常穿何衣?”福顺舔舔嘴唇。
沈清辞把十两银子放在他手心。银子沉,福顺的手往下坠了坠。他攥紧,四下张望,
才凑到沈清辞耳边:“每月十五,陛下会去忆月阁,一个人,对着林姑娘的画像喝酒,
谁都不让进。”“常穿的……有件旧龙袍,杏黄色的,左边袖口破了道口子。尚衣局要补,
陛下不让,就一直穿着。”“还有,陛下这两年信丹药,有个道士常进宫。
吃了丹药脾气更坏,上个月打死了两个太监。”福顺顿了顿,又想起什么:“对了,
怪事——陛下每次穿那件旧龙袍前,都会把袖口凑到鼻子前闻一下。像在闻什么味道。
”沈清辞心脏猛地一跳。“什么味道?”“不知道,离得远。”福顺摇头,“反正每次闻完,
陛下眼神就有点……不对劲。”银子收好,福顺要走,又回头:“你打听这些干什么?
”“寻亲。”沈清辞说,“母亲临终前说,婉姨在宫里留了东西给我。”“东西?
”福顺皱眉,“林姑娘的东西,早被陛下收走了。忆月阁里全是她的旧物,旁人碰不得。
”“碰不得,看看总行。”福顺走了。沈清辞站在柳树下,护城河的水黑沉沉,
映着零星灯火。他从怀里掏出母亲的密信,撕下空白一角,咬破指尖,用血写:“袖口有异,
或藏毒物残留。”血字很小。他把纸条卷起来,塞进玉簪的空心处。簪身有极细的缝,
刚好够塞进纸卷。做完这些,他靠着柳树滑坐在地。三天没正经吃饭,胃里空得发慌。
怀里还剩五个铜板,够买一碗粥。但他没动。饿着。饿让人清醒。***殿试那天,
沈清辞起得很早。他用最后五个铜板买了劣质香料——檀香、薄荷、一点陈年梅花干。
在客栈后院支起小炉,慢慢熬。味道不对。林婉用的“冷梅香”是江南特制,
清冽里带一丝苦。他手里的材料粗糙,熬出来只有烟熏火燎的呛。他盯着炉火,
突然想起母亲说过:林婉调香,会在最后加一滴白醋,压住烟火气。客栈没有白醋。
他走到厨房,找到半坛腌菜的酸水。滴进去。味道变了。虽不精致,
但那股清苦的底子出来了。他把香料碾成粉末,用纱布包好,塞进衣襟内侧。体温烘着,
极淡的香气一点点渗出来。殿试在崇政殿。三百考生,鸦雀无声。萧彻迟到了半个时辰。
他进来的时候,沈清辞抬眼瞥了一下——四十出头,眼袋很重,龙袍穿得松松垮垮。
坐下就撑着头,一副没睡醒的样子。考官发卷。策论题目:《论边患》。沈清辞提笔。
他刻意换了左手写字,字迹工整但稚嫩,像初学者。内容迎合萧彻的好大喜功,
提议“修建通天高台,镇四方国运”。写完后,他在卷子边缘,
用左手极淡的墨迹添了一行小字:“夜雨残荷,旧影如刀。”墨里掺了水,
字迹浅得几乎看不见。他故意让一滴墨晕开,染糊了“刀”字的最后一笔。像无意滴落的。
交卷时,他排在末尾。前面的人一个个上前,萧彻看都不看,只挥挥手。轮到沈清辞,
他躬身,双手呈上卷子。冷梅香飘出来。极淡,混在殿里的檀香里,几乎闻不见。
但萧彻动了。他猛地坐直,眼睛死死盯住沈清辞的脸。手里的酒杯“哐当”掉在地上,
酒液溅湿龙袍下摆。太监要去捡,萧彻抬手制止。大殿静得可怕。萧彻站起来,
一步步走下御阶。他在沈清辞面前停住,手指抬起沈清辞的下巴。力道很重,指甲掐进肉里。
“你……”萧彻的声音在抖,“你母亲,是林氏何人?”沈清辞垂眸:“远房表亲。
母亲曾说,婉姨最爱‘夜雨残荷’之景,可惜……”“可惜什么?”萧彻急问,手指收紧。
沈清辞抬眼。四目相对。他在萧彻眼睛里看到了很多东西:疯狂、怀念、恐惧,
还有一丝扭曲的欲望。“可惜雨打残荷声,”他轻声说,“像极了箭矢破空。
”萧彻的脸瞬间煞白。他松开手,踉跄退了一步。太监赶紧扶住。“你……”萧彻喘了口气,
“叫什么名字?”“草民沈清辞。”“沈、清、辞。”萧彻一字一顿念,像在咀嚼,“好,
好名字。从今日起,你是御前侍读,即刻入宫。”“谢陛下隆恩。”跪下叩首时,
沈清辞袖中的指甲掐进掌心。疼。父亲,我进去了。刚起身,
里突然响起碎响:检测到“历史直觉”天赋解锁隐藏能力:记忆残影每日限三次,
可看见物品承载的强烈记忆片段他下意识看向地上那只打翻的酒杯。金杯,杯壁雕着蟠龙。
视线聚焦的瞬间,酒杯周围浮起一层朦胧的光晕——画面闪进来。还是这只酒杯,
被一只苍老的手握着。手的主人在咳嗽,咳得撕心裂肺。另一只手伸过来,
往酒杯里抖进一撮白色粉末。粉末遇酒即溶。那只手把酒杯推回去:“皇叔,喝了吧,
喝了就不咳了。”苍老的手颤抖着接过,仰头饮尽。下一秒,七窍流血。画面碎了。
沈清辞收回视线,背上沁出一层冷汗。那只下毒的手,
拇指戴着一枚翡翠扳指——和此刻萧彻手上那枚,一模一样。“沈侍读。
”太监总管的声音在耳边响起。沈清辞抬眼。总管五十来岁,面白无须,眼睛细长。
他打量沈清辞的脸,目光像刷子,一寸寸刷过眉骨、鼻梁、嘴唇。“好相貌。”总管笑了,
笑容里没什么温度,“皇后娘娘最喜俊俏少年。明日记得去长春宫请安,别误了时辰。
”“是。”“跟咱家来吧,给你安排住处。”侍卫房在西华门边上,窄小的一间,
除了一张板床、一张桌子,什么都没有。窗户纸破了,冷风灌进来。
总管站在门口:“今日先歇着。明日辰时,有人带你去见陛下。”门关上。脚步声远了。
沈清辞走到桌前,桌上有一面铜镜,蒙着灰。他用袖子擦干净。镜子里映出一张脸。
少年的脸。苍白,瘦削,眉眼清秀得过分。唇色很淡,睫毛很长——这些是陆清棠的痕迹。
但轮廓硬了。下颌线分明,喉结凸出,肩膀的线条撑起了粗麻布衣。他伸手摸自己的脸。
皮肤是凉的。指尖划过眉骨、颧骨、下巴。陌生的触感。“清棠已死。
”声音从喉咙里发出来,低沉,带着少年的沙哑。他对着镜子,一字一句:“我是沈清辞。
”“佞臣沈清辞。”镜子里的人眼角抽动了一下。一滴泪滑下来,滚过脸颊,
在下巴处悬了一会儿,滴在桌面上。“啪。”极轻的一声。他抬手擦掉泪痕,指尖湿漉漉的。
低头看,桌面上那滴泪渍旁边,
起一行只有他能看见的小字:倒计时:1094天23小时58分字迹泛着微弱的红光,
像血,像炭火将熄前的余烬。窗外,更夫敲梆子。三更天了。
# 第二章:双面·罪证·生死劫天还没亮透,雾是青灰色的。沈清辞和衣躺在板床上,
一夜没闭眼。窗纸破洞处透进一点冷光,在地面切出个歪斜的四边形。他盯着那光看,
看灰尘在光柱里浮沉。更夫敲四更梆子的时候,门外传来脚步声。不是一个人,是一串。
细碎、急促,像许多只脚踩在石板上。他坐起来。门被推开,没敲。
两个小太监一左一右站在门口,中间是个穿藕荷色比甲的宫女,二十出头,脸盘圆润,
眼皮耷拉着。“沈侍读。”宫女开口,嗓音尖细,“皇后娘娘召见。”现在?辰时请安,
此刻刚过寅时。宫里的规矩,皇后不会这么早见人。沈清辞下床,躬身:“敢问姐姐,
娘娘有何吩咐?”宫女眼皮抬了抬:“去了就知道。”没给他换衣裳的时间。
两个小太监一前一后夹着他,宫女走在前头,步子迈得又快又轻,像脚不沾地。
长春宫在御花园东侧。雾还没散,廊檐下的灯笼晕开一圈圈昏黄。沿途遇见几队巡逻的侍卫,
看见宫女腰牌,都低头让路。没人说话。只有脚步声,还有远处隐约的鸟叫,一声,又一声,
叫得人心慌。长春宫正殿比想象中小。帘子重重,空气里一股浓腻的檀香味,混着药味。
皇后坐在暖榻上,三十五六岁模样,穿家常的鹅黄襦裙,没戴冠,头发松松挽着。
她手里捏着一串佛珠,一颗一颗拨。“臣沈清辞,叩见皇后娘娘。”沈清辞跪下去。
佛珠停了一瞬。“抬头。”他抬脸。皇后的目光落在他脸上,从上到下,从左到右,
看了很久。那目光不是看人,是看物件,看纹路,看瑕疵。“果然像。”皇后说,
声音平平的,“昨夜陛下提起你,说林婉的表亲入宫了。本宫还奇怪,林家哪还有表亲。
”佛珠又开始拨。“你母亲叫什么?”“林氏,单名一个芸字。”“林芸。”皇后重复一遍,
“没听过。哪一支的?”“旁支远亲,祖上迁到北地,早已没落。”沈清辞垂眼,
“母亲临终前才说,与婉姨有旧。”“临终前……”皇后笑了,笑声很短,
像喉咙里卡了东西,“那还真是巧。”她端起榻边小几上的茶盏,抿了一口,放下。“赐茶。
”宫女端来另一盏茶,青瓷荷叶杯,冒着热气。递到他面前。沈清辞接过来,茶汤澄黄,
茶香清冽——是上好的雨前龙井。但味道里掺着一丝极淡的涩,像杏仁皮被碾碎后的苦。
他没喝。记忆残影还能用两次。他盯着茶杯,视线聚焦。杯壁浮起光晕——画面闪进来。
还是这只杯子,被一个少年捧着。少年十七八岁,穿御前侍读的青色官服,脸色苍白。
他小口抿茶,喝得很慢。喝完第三口,他放下杯子,对座上的皇后行礼:“谢娘娘赏。
”皇后笑着点头。少年退出去。走到殿门口,脚步踉跄了一下,扶住门框。画面快进。
少年倒在回廊里,七窍流血,手指抠进石板缝。血从眼睛、鼻子、嘴巴里涌出来,黑红色的,
稠得像浆。画面碎了。沈清辞手一抖,茶汤晃出来,烫到手背。“怎么了?”皇后问。
“臣……”他吸了口气,“臣惶恐。陛下昨日赐了丹药,命臣每日晨起先服丹,再进饮食。
臣不敢违旨。”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瓷瓶。萧彻昨天随手给的,说是“养神丹”,
其实是普通参丸,无毒。倒出一粒,当着皇后的面,吞下去。喉结滚动。皇后盯着他的喉咙,
看了三息,移开视线。“好个忠仆。”她放下佛珠,“陛下身边的人,
本宫自然要替陛下照料周全。但你初入宫闱,许多规矩不懂,需得有人提点。
”她朝那宫女抬了抬下巴:“春桃,带沈侍读去‘静思堂’,把宫里的规矩,好好说给他听。
”“是。”静思堂是个耳房,没窗,只有一扇厚重的木门。春桃把他推进去,门从外面闩上。
“沈侍读在此静思,明日辰时,奴婢来接您。”脚步声远了。黑暗吞没一切。
沈清辞站在原地,等眼睛适应。过了约莫半刻钟,才勉强看清轮廓——房间四四方方,
空空荡荡,墙角堆着几个蒲团,满是灰。空气里有股霉味,混着旧木头和灰尘的气息。
他走到门边,摸门板。厚实,外头包了铁皮,推不动。门闩的位置很高,从里面够不着。
他坐下,背靠墙。黑暗让人耳朵变尖。远处有打更声,有巡逻的脚步声,
有风吹过屋檐的呜咽。还有老鼠在梁上跑,窸窸窣窣。他闭上眼。不是休息,是算时间。
从进长春宫到现在,约莫两刻钟。皇后为什么关他?试探?折磨?
还是单纯想让他错过今日面圣?萧彻会找他吗?不知道。他对宫里的局势一无所知。
皇后与萧彻的关系,后宫的派系,太监宫女的站队——全是空白。唯一能倚仗的,
只有这张脸,和那三次能力。还有,得找自己人。一个人走不了多远。他想起福顺,
那个贪财的小太监。还有母亲密信里的翠姑——西六所洒扫婢女,林婉的旧人。得出去。
***不知道过了多久,门外传来开锁声。门推开,天光刺进来。沈清辞眯起眼,
看见春桃站在门口,手里提着一盏灯笼——天还没亮?“沈侍读,请吧。”他站起来,
腿麻了,踉跄一步。春桃没扶,转身就走。又是那串细碎的脚步声,穿过回廊,穿过宫门,
最后停在一处小院前——是他昨日的侍卫房。“今日陛下召见,辰时二刻,乾清宫。
”春桃说完,走了。沈清辞推门进去。桌上放着一套新的官服,青色,叠得整整齐齐。
旁边有一盆冷水,一块布巾。他脱掉粗麻衣,换上官服。料子细软,尺寸刚好,腰身收得紧。
铜镜里,青衫少年,眉目清冷,倒真像那么回事。辰时一刻,有小太监来引路。
乾清宫比崇政殿更压抑。帘幕深垂,光线昏暗,空气里有股丹药的焦苦味,
还有隐隐的腥气——像什么东西烧糊了,又像血。萧彻坐在书案后,穿那件旧龙袍。
左手袖口的破损处,用金线粗粗缝了几针,针脚歪斜。他正在批奏折,朱笔悬着,迟迟不落。
“陛下,沈侍读到了。”太监通报。萧彻抬头。他的眼睛里有血丝,眼袋发青,
一看就是没睡好。看见沈清辞,眼神恍惚了一下,随即聚焦。“过来。”沈清辞走近,
在书案前三步停下。萧彻放下笔,身子往后靠,上下打量他。目光很重,像有实质,
刮过皮肤。“昨夜睡得好吗?”“回陛下,尚可。”“长春宫那边……”萧彻顿了顿,
“皇后为难你了?”“皇后娘娘慈和,赐茶教导,是臣的福分。”“福分。
”萧彻重复这个词,嘴角扯了扯,“你倒会说话。”他拿起案上一本奏折,扔过来。
沈清辞接住。“看看。”翻开。是吏部侍郎李崇的折子,弹劾工部贪污河工银两,言辞激烈,
末尾一句:“陛下若再纵容,则国将不国。”沈清辞记得这个名字。三年前陆家下狱,
满朝噤若寒蝉,只有三个人上折求情。李崇是其中一个。“李崇。”萧彻敲了敲桌面,
“此人仗着是先帝老臣,屡屡顶撞。昨日又当庭驳朕的面子。”他盯着沈清辞:“你去查他。
贪赃枉法,结党营私,随便什么罪名,找出来。三日后,朕要看到罪证。”空气凝住了。
丹炉里炭火噼啪一声,炸出几点火星。沈清辞垂眼,看奏折上的字。李崇的笔迹刚劲,
每一划都力透纸背,像要把纸戳破。选项A:照做。可得萧彻深度信任。
选项B:阳奉阴违。风险极大。他沉默了三息。“臣遵旨。”他说,“但臣有一言,
不知当讲不当讲。”“讲。”“李崇是三朝老臣,门生故旧遍布朝野。若以寻常罪名治他,
恐难服众,反惹清议沸腾。”沈清辞抬起头,“陛下若真想除他,不如换个法子。
”萧彻眯起眼:“什么法子?”“李崇最重名节。陛下可下旨褒奖他‘忠直敢言’,
调任闲职,明升暗贬。再让人散播流言,说他表面刚正,实则贪墨——无需实证,
风言风语足矣。半年之内,他的名声自毁,届时陛下再寻个由头罢黜,无人会为他说话。
”他顿了顿,声音压低:“杀人诛心。陛下,让他活着看自己身败名裂,比一刀杀了,
更解恨。”萧彻没说话。炭火又炸了一下。良久,萧彻笑出声。笑声干涩,像枯树枝折断。
“沈清辞。”他说,“你比朕想的,更有意思。”“臣惶恐。”“就按你说的办。
”萧彻挥挥手,“去拟旨吧。褒奖的旨意,你亲自写。”“是。”沈清辞退到偏殿,
太监备好笔墨。他提笔,写“吏部侍郎李崇,忠悃素著,风骨凛然……”写一个字,
胃里绞一下。李崇今年六十二岁。陆清棠小时候见过他,骑一匹瘦马,穿洗得发白的官服,
去城郊施粥。父亲说他“穷得只剩一身骨头”。那身骨头,现在要被他亲手敲碎。
笔尖悬在“然”字最后一捺,墨聚成滴,将落未落。他吸了口气,笔锋一转,
在“风骨凛然”后,添了一句极小的夹注:“弘光元年,江北大旱,李崇散尽家财购粮,
活民三千。其妻簪珥皆典,冬日无棉。”字小如蝇头,墨色极淡,写在行距之间。
除非贴得很近,否则看不见。写完,他搁笔。旨意送到李崇府上时,已是黄昏。
沈清辞远远站在街角,看李崇跪在门口接旨。老人脊背挺得笔直,听完褒奖,叩首,
起身时晃了一下。管家扶住他。李崇抬头,望向皇宫方向,看了很久。沈清辞转身离开。
夜里,他托了一个倒夜香的老太监,捎出去十两银子——他最后一点钱。“给李大人府上。
什么也别说。”老太监捏着银子,浑浊的眼睛看了他一眼:“沈侍读,这钱烫手。
”“我知道。”“知道了还送?”沈清辞没回答。老太监叹了口气,把银子揣进怀里,
推着粪车,吱呀吱呀走了。***第二天,沈清辞“病”了。病来得突然。
晨起去乾清宫当值,走到半路,脸色煞白,额角冒冷汗,扶着宫墙吐了一地清水。
小太监慌忙去报。太医署来了个小学徒,十六七岁,瘦瘦小小,背个药箱。进了侍卫房,
搭脉,翻眼皮,问诊。屋里没别人。小学徒搭脉的手指很凉。搭着搭着,指尖忽然一顿。
沈清辞腕上有旧伤——镣铐磨出的疤,深褐色,像一条蜈蚣盘在腕骨上。疤被袖子遮着,
刚才吐的时候,袖子滑上去一点。小学徒盯着那道疤,手开始抖。“你……”他声音发颤,
“这伤……”沈清辞睁开眼。“小兄弟贵姓?”“姓安,家里行三,叫小安。
”小学徒低着头,不敢看他。“小安。”沈清辞慢慢坐起来,“你师父是陈太医吧?三年前,
陈太医因‘误诊’被杖毙,其实是因为他给陆家女眷看过伤,是不是?”小安猛地抬头,
眼睛瞪圆。“你……你怎么……”“陆史官生前说过,陈太医有个小徒弟,心善,
曾偷偷给牢里的陆家人送伤药。”沈清辞看着他,“是你吗?”小安的眼泪涌出来,
大颗大颗往下砸。他捂住嘴,不敢哭出声,肩膀一耸一耸。沈清辞等他哭完。
“我现在叫沈清辞,御前侍读。”他说,“我需要一个太医署的眼线。”小安跪下来,
额头磕在地上:“陆姑娘……不,沈大人,您还活着……”“活着。”沈清辞扶他起来,
“但活不了多久,如果没人帮我。”“我帮!我帮!”小安擦眼泪,“师父死前说,
陆家是冤枉的……可我人微言轻,什么也做不了……”“现在你能做了。”沈清辞压低声音,
“陛下服的丹药,你能接触到吗?”“能。丹药是凌云观道士炼的,每次送来,
太医署要查验。我负责登记造册。”“查过成分吗?”“查过。”小安凑近,声音压得更低,
“里头有汞,还有朱砂,剂量很大。长期服用,会损神智,伤肝肾。我跟署正大人禀报过,
大人让我闭嘴,说陛下信这个,谁劝谁死。”汞。朱砂。沈清辞记下了。“还有一件事。
”他说,“陛下每次服丹后,会去一个密室。你知道密室在哪儿吗?
”小安摇头:“只听师父提过一次,说陛下服丹后性情最暴,常独自去‘那个地方’。
钥匙……钥匙好像在陛下常穿的旧龙袍内衬里。”旧龙袍。又是那件袍子。
***机会来得比想象中快。七日后,萧彻去汤泉宫沐浴。走前,他把旧龙袍脱下,
扔给沈清辞:“拿着,等朕回来。”袍子沉甸甸的,
带着体温和一股复杂的味道——丹药的焦苦,熏香的甜腻,还有隐隐的汗味。
沈清辞躬身接过。萧彻走了,太监宫女跟了一大串。屋里只剩他一个人。门关着。
他走到窗边,借着光,仔细看这件龙袍。杏黄色,缎面织金,但已经旧了,光泽黯淡。
左边袖口那道口子,金线缝补的针脚粗陋,像条蜈蚣趴在那儿。他伸手,摸内衬。
袍子有三层,最里层是细棉布。手指沿着缝线一点点探,在左肋下方,
摸到一处——针脚密度不一样,更紧,更密。拆开这里,应该能找到夹层。但他没动。
先用了记忆残影。今日还剩两次。视线聚焦袖口破损处。光晕浮起——画面涌进来。
猎场。秋日,天高云淡。年轻的萧彻那时还是二皇子挽弓射鹿,箭矢破空,鹿应声倒地。
一个穿明黄骑装的男子拍手大笑,走过来拍他的肩:“二弟好箭法!”是先太子萧恒。
萧彻笑着转身,袖口拂过箭囊。有一支箭的箭头,在阳光下泛着诡异的蓝光。画面跳转。
还是猎场,但天色暗了。萧恒中箭倒地,胸口插着的,正是那支蓝头箭。萧彻跪在旁边,
握住他的手,眼泪掉下来:“皇兄……皇兄……”萧恒嘴唇翕动,说了句什么。萧彻凑近听。
听完,他脸上的悲痛一点点凝固,变成某种扭曲的东西。他慢慢松开萧恒的手,站起来,
从自己袖子里抽出一块帕子,擦了擦指尖沾的血。然后把帕子扔在萧恒脸上。画面再跳。
深夜,书房。萧彻已经是皇帝了坐在灯下,手里拿着一小包白色粉末。
他把粉末倒进酒杯,推给对面一个白发老者。老者颤抖着喝下。七窍流血。萧彻看着尸体,
从怀里掏出一张纸,用朱笔在“鲁亲王”三个字上打了个叉。画面碎了。沈清辞呼吸发紧。
第二次能力,用在袍子内衬那处异样上。光晕再次浮起——这次是静态画面。萧彻坐在榻上,
就着烛火,把一张泛黄的纸塞进龙袍内衬。纸上有字,列着一排名字。
最上面一行写:“必除之臣十二人”。第三个名字:陆明渊。沈清辞父亲的名字。
纸的右下角,还有一行小字:“知情者尽诛,勿留后患。”画面碎了。他站在原地,
手心全是汗。袍子很沉,沉得像具尸体。拆,还是不拆?拆了可能找到物证——那张名单,
那包毒粉。但萧彻随时可能回来,一旦发现线脚被动过,就是死。不拆,错过这次,
下次不知何时。他盯着那处针脚看了三息,从怀里掏出一把小刀——日常用来裁纸的,
刃很薄。刀尖挑进缝线。线是丝线,韧性很强。他挑得很慢,一点一点,挑开半寸长的口子。
手指伸进去,摸到纸张粗糙的质感。夹层里果然有东西。先掏出来的是一张纸。泛黄,
折了三折。展开,十二个名字,墨迹深浅不一,最早的名字已经晕开了。陆明渊那一行,
墨色最新。他把纸折好,塞回怀里。再摸,摸到一个小油纸包,拇指大小。打开,
里面是白色粉末,细如面粉,无味。毒药。他包好,也揣进怀里。
现在的问题是:怎么把拆开的地方缝回去?针线盒在书案抽屉里。他翻出来,选最细的针,
穿上线——线是金色的,和原来的线颜色相近,但新线光泽更亮。没办法,
只能赌萧彻不会细看。他坐下来,就着窗光,一针一针缝。手稳,针脚尽量模仿原来的粗糙。
但新线太亮,在旧缎子上像一道疤。缝到一半,门外传来脚步声。不是一个人,是一群。
萧彻回来了。沈清辞手一抖,针扎进指尖。血珠冒出来,他迅速把针线塞进袖口,
袍子团起来抱在怀里,起身。门推开。萧彻披着浴袍,头发湿漉漉散着。他脸色潮红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