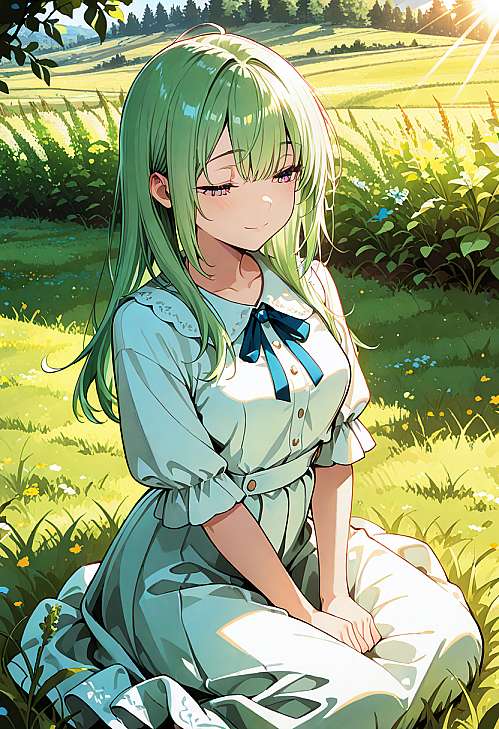江柔觉得今天的阳光特别好,好到足以照亮她发髻上那支金累丝嵌红宝石的步摇。
作为新晋的官太太,她觉得自己有义务去“关照”一下那个被扫地出门的嫡姐。
听说那女人现在沦落到在西市卖肉?真是丢尽了江家的脸面。“一会儿见了她,
记得把鼻子捂上。”江柔坐在软轿里,漫不经心地吩咐外面的丫鬟,
“那种市井之地的腥臭气,最是容易沾染到我这身蜀锦上,回头老爷闻到了要心疼的。
”丫鬟翠儿连忙点头,一脸谄媚:“夫人说得是,那种粗鄙之人,哪配见您啊。咱们这次去,
是给她脸,施舍她几两碎银子,免得她饿死在街头,回头还连累了老爷的名声。
”江柔捂嘴轻笑,眼神里满是猫捉老鼠般的戏谑。她甚至已经想好了一会儿的开场白,
要先叹气,再流泪,最后无奈地扔下银子,转身留下一个完美的背影。这剧本简直完美。
只是她万万没想到,她猜中了开头,却没猜中那把正剁在案板上、还冒着热气的杀猪刀。
1西市的吵闹声像是一锅煮沸了三天三夜的泔水,各种味道混杂在一起,
形成了一种极具杀伤力的生化武器。我站在油腻腻的案板前,
手里握着一把重达三斤六两的玄铁杀猪刀,正专心致志地处理眼前这扇刚送来的半扇猪肉。
对我来说,这不是切肉,这是一场精密的地质勘探。刀锋顺着肌理滑下去的手感,
美妙得像是拆解敌人的关节,每一次脂肪与筋膜的分离,都代表着一次外交谈判的全面胜利。
“老板娘,来两斤五花,要肥瘦相间的!”一个满脸横肉的大汉把几枚铜钱拍在案板上,
震得上面的苍蝇进行了一次紧急战术起飞。我抬起眼皮,扫了他一眼。
这一眼里包含了三分薄凉、三分讥笑和四分漫不经心,
精准地复刻了当年我爹在战场上看敌军俘虏的神情。“排队。”我嘴里吐出两个字,
声音不大,但带着一股子常年在血腥味里浸泡出来的凉意。大汉愣了一下,刚想发作,
视线就落在了我手里那把正在滴油的刀上。
那刀尖距离他按在案板上的手指只有零点零一公分。这是一个充满了哲学意味的距离,
它探讨了“生存还是毁灭”这个终极命题。大汉咽了口唾沫,乖乖地缩回手,
站到了旁边那个正在挖鼻孔的小屁孩后面。很好,维护地区和平靠的永远不是嘴皮子,
而是战略核威慑。我满意地收回视线,手起刀落。“咔嚓”一声脆响。
一根坚硬的猪肋骨被我整齐地斩断,切口平滑得像是被御林军精心保养过的大理石地面。
周围看热闹的人群发出了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,仿佛那一刀砍在了他们自己的脖子上。
我很享受这种氛围。这种混合了恐惧、敬畏和食欲的复杂气场,
比当年在将军府里闻那些虚伪的脂粉气要舒坦一万倍。
就在我准备进行下一步“心肺复苏式”的掏心操作时,
人群忽然像是被摩西分海一样自动让开了一条道。
一顶粉嫩得像是刚出生小乳猪皮肤一样的软轿,带着一股廉价但浓烈的香气,
大摇大摆地停在了我的肉铺门口。轿帘掀开,一只手伸了出来。那手保养得极好,
指甲上染着鲜红的蔻丹,像是刚从死人堆里刨出来似的,透着一股妖异的喜庆。紧接着,
一张我做梦都想拿鞋底子抽八百遍的脸露了出来。江柔。我同父异母的好妹妹,
踩着我将军府满门尸骨上位的状元夫人。她今天穿得像个移动的珠宝展示台,满头金翠乱颤,
生怕别人不知道她刚发了一笔断子绝孙的横财。“哎呀,姐姐,真是让妹妹好找啊。
”她拿帕子掩着鼻子,声音娇滴滴的,像是嗓子眼里卡了一口二十年的陈年老痰,
听得人天灵盖发麻。我没说话,只是慢条斯理地拿起旁边一块油乎乎的抹布,
开始擦拭我的刀。那抹布已经黑得看不出原色了,上面混合了猪油、血水和岁月的沧桑,
是我店里除了刀之外的第二大镇店之宝。江柔看着那块抹布,眼角抽搐了一下,
往后退了半步。“姐姐,你怎么沦落到这种地步了?要是爹爹在天有灵,看到你这个样子,
怕是要心疼坏了。”她一边说,一边假惺惺地红了眼眶,演技之浮夸,
简直是对我们大梁戏剧行业的公开侮辱。我终于擦完了刀。
刀刃在阳光下反射出一道森冷的寒光,正好晃在了江柔那张涂了三斤粉的脸上。
“要买肉就排队,不买就滚。”我把刀往案板上一剁,入木三分。“别耽误老子赚钱。
”2江柔显然没料到我的反应如此直接且粗暴。在她那贫瘠的大脑构想里,
我应该是跪在地上抱着她的大腿痛哭流梯,求她赏口饭吃,或者是羞愤欲绝地掩面而逃。
唯独没想到,我会像个没事人一样,把她当成一坨阻碍交通的不可回收垃圾。“姐姐,
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?”江柔深吸了一口气,调整了一下面部表情,
切换到了“忍辱负重小白花”模式。“我知道你心里有怨,怪文宣哥哥休了你。
可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啊,姜家犯了那么大的事,文宣哥哥身为朝廷命官,总不能受牵连吧?
”她这话说得极有水平。既点出了我“弃妇”的身份,又强调了赵文宣“大义灭亲”的无奈,
顺便还踩了一脚我死去的爹。周围的吃瓜群众顿时竖起了耳朵。
人类对于豪门八卦的热衷程度,要远远高于对猪肉价格波动的关心。我冷笑一声,
从旁边的水桶里捞出一块刚洗干净的猪大肠。这玩意儿虽然洗干净了,
但那股子直冲天灵盖的味道依然保留着原始的野性。我拎着大肠,在手里晃了晃,
那滑腻腻的触感像极了赵文宣那个软饭男的良心。“江柔,你脑子里是不是也装了这玩意儿?
”我指了指手里的猪大肠,一脸诚恳地问道。“装了什么?”江柔下意识地问道。“屎啊。
”我回答得理直气壮。“姜家被抄家是因为什么,你那个当师爷的爹心里没数吗?
赵文宣能考上状元,花的是谁的银子,穿的是谁的衣裳,他晚上做梦的时候没被鬼压床吗?
”我每说一句,就往前走一步。江柔被我逼得连连后退,脸色由红转白,又由白转青,
变脸速度堪比川剧大师。“你……你粗俗!无耻!”她憋了半天,
终于憋出了两个毫无杀伤力的形容词。“我粗俗?”我笑了。
我直接把手里的猪大肠“啪”的一声摔在案板上,那动静大得像是在公堂上拍惊堂木。
汁水四溅。几滴不明液体精准地飞到了江柔那身价值连城的蜀锦上,
迅速晕染开一朵朵带着异味的梅花。“啊!!”江柔发出了一声尖叫,
那分贝高得能把方圆五里的公鸡都吓得提前打鸣。“我的衣服!这可是贡品!
姜离你这个疯婆子,你赔我!”她终于装不下去了,五官扭曲在一起,
像是一个发酵失败的馒头。“赔?”我抱起胳膊,上下打量着她。“行啊,算算账吧。
当年你爹借住我将军府,吃了十年白饭,按照现在的物价,算上通货膨胀和精神损失费,
打个八折,你给我三万两,这衣服钱我就赔你。”我伸出三根手指,在她面前晃了晃。
江柔气得浑身发抖,指着我的鼻子,手指上那些金戒指撞得叮当乱响。“你……你做梦!
来人!给我砸!把这个破摊子给我砸了!”她歇斯底里地吼道,
完全忘了自己刚才还是个柔弱不能自理的官太太。几个家丁模样的男人从后面冲了出来,
一个个挽起袖子,一脸凶相。看来今天这场“国际冲突”是无法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了。
我叹了口气,伸手摸向了案板下面那根用来通下水道的铁棍。虽然我现在是个卖肉的,
但也别忘了,我也曾经是能拉开两石强弓的将门虎女。既然你们非要送人头,
那我就勉为其难地刷个战绩吧。3战斗结束得比我预想的还要快。
大概就是我切完半斤里脊肉的时间。那几个家丁此时正躺在地上,
摆出各种充满了现代艺术感的姿势,呻吟声此起彼伏,组成了一首不太和谐的交响乐。
我其实没下狠手。只是用了点巧劲,卸了他们几个关节,
顺便帮他们疏通了一下常年淤堵的经络。这叫物理治疗,他们应该付我诊金才对。
江柔已经傻了。她呆呆地站在原地,嘴巴张得能塞进去一个生鸡蛋,
眼神里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怀疑。在她的认知里,女人打架应该是扯头发、抓脸、吐口水,
而不是像我这样,单手拎起一个一百八十斤的壮汉,像扔沙包一样扔出去三丈远。
“你……你别过来!”见我提着铁棍朝她走去,江柔终于回过神来,发出了一声惨叫,
脚下一软,直接瘫坐在了地上。地上很脏,全是油污和烂菜叶子。但她已经顾不上这些了,
两只手撑在地上,拼命往后挪,活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吉娃娃。“姐姐!我错了!姐姐饶命!
”她哭得梨花带雨,妆都花了,两道黑色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,
看起来像是刚从煤窑里爬出来的鬼。我在她面前停下脚步,居高临下地看着她。
“刚才不是还要砸我店吗?怎么,这么快就改变战略部署了?”我用铁棍挑起她的下巴,
冷冷地问道。“不砸了!不砸了!是妹妹有眼不识泰山!妹妹猪油蒙了心!”江柔拼命摇头,
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。我撇了撇嘴,顿时觉得索然无味。这就是所谓的宅斗高手?
就这点心理素质?我还没开大呢,她就直接投降了,这让我很没有成就感。“行了,别嚎了。
知道的是你在认错,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这儿是屠宰场呢。”我嫌弃地收回铁棍,
在身上擦了擦。“回去告诉赵文宣,让他把脖子洗干净了。欠我的账,我会一笔一笔跟他算。
今天这只是利息,下次再敢来我这儿撒野,我就不是卸关节这么简单了。”我微微弯腰,
凑到她耳边,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道:“下次,我会把你身上的零件,
一个一个地拆下来,挂在门口当腊肉。”江柔浑身一僵,瞳孔剧烈收缩,然后两眼一翻,
非常干脆利落地晕了过去。啧,心理承受能力太差。这届反派不行啊。我站直身子,
对着那几个还在地上哼哼的家丁踢了一脚。“别装死了,带着你们主子,滚。
”家丁们如蒙大赦,忍着痛爬起来,七手八脚地抬起晕死过去的江柔,像一群战败的逃兵,
灰溜溜地跑了。围观群众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。我淡定地拱了拱手,深藏功与名。
“老板娘,牛逼!”刚才那个买肉的大汉竖起了大拇指,一脸崇拜。“过奖过奖,基本操作。
”我谦虚地笑了笑,转身回到案板前,继续我未完成的地质勘探工作。只是心里清楚,
今天这事儿,没完。打了小的,老的肯定会来。赵文宣那个伪君子,最是要面子。
我今天把他的宠妾整成这样,无异于在他脸上刻了“窝囊废”三个字。
他肯定会来找回场子的。想到这里,我不由得兴奋起来,手里的刀挥舞得更快了。来吧,
快来吧。我的大刀已经饥渴难耐了。4果不其然,江柔前脚刚被抬回去,
下午赵文宣就杀到了。这速度,比现代的外卖配送都要快,
充分体现了仇恨是第一生产力这个真理。不过这次他没带家丁,
而是带了两个穿着官服的衙役。看来是打算动用国家机器对我进行降维打击了。
赵文宣穿着一身崭新的官袍,胸前绣着孔雀补子,头戴乌纱,人模狗样的,
确实有那么几分衣冠禽兽的味道。只是那张脸,阴沉得能滴出水来。“姜离!你可知罪?!
”他一进门,就摆出一副公堂审案的架势,指着我厉声喝道。我正坐在门口的板凳上啃黄瓜,
听到这话,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“哟,这不是赵大人吗?稀客啊。”我咬了一口黄瓜,
清脆的声音在安静的店铺里显得格外刺耳。“怎么,家里肉吃完了?
还是说江柔那个小身板满足不了你,需要来我这儿补补肾?”我这话说得极其露骨,
周围围观的百姓顿时发出一阵哄笑。赵文宣的脸“刷”的一下就红了,
不知道是气的还是羞的。“你……你一个妇道人家,怎可说出如此污言秽语!
简直……简直有辱斯文!”他抖着手指着我,一副被玷污了的圣女模样。“斯文?
”我把剩下的半截黄瓜扔进泔水桶里,站起身,拍了拍手。“赵文宣,你跟我谈斯文?
当初你为了攀高枝,设计陷害我爹,害我姜家满门抄斩的时候,你怎么不谈斯文?
现在穿上官服装人了?别忘了,你骨子里就是条喂不熟的狗。”我的声音不大,
但每个字都像是钉子一样,死死地钉在他的七寸上。赵文宣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,
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。他做贼心虚。姜家的事,虽然表面上是皇帝下旨,
但背后少不了他的推波助澜和伪证。这是他一辈子洗不掉的污点,
也是他最怕被人提起的痛脚。“你……你胡说八道!朝廷定的案,岂容你信口雌黄!
”他色厉内荏地吼道,试图用声音掩盖心虚。“来人!把这个刁妇给我拿下!
带回衙门严加审问!”那两个衙役听了命令,犹豫着拔出腰刀,朝我逼了过来。
他们也是老油条了,看得出来这事儿不简单,所以动作慢吞吞的,充满了摸鱼的智慧。
“我看谁敢!”我冷喝一声,从身后摸出了那把杀猪刀。阳光下,刀锋闪烁着嗜血的光芒。
“赵文宣,你今天敢动我一下试试。光脚的不怕穿鞋的,我姜离现在就是烂命一条。
你要是想拿你的锦绣前程来换我这条命,那我绝对奉陪到底。”我一边说,
一边用拇指轻轻刮了刮刀刃。这个动作充满了暗示性。既像是在检查武器的锋利度,
又像是在预演割断某人喉咙的过程。赵文宣怂了。他这种人,最是惜命。
好不容易爬到这个位置,他可不想因为一个弃妇把自己搭进去。“你……你简直是不可理喻!
”他咬牙切齿地憋出一句话,挥手让那两个如释重负的衙役退下。“姜离,你别得意。
今天本官不跟你一般见识。但你打伤柔儿的事,必须给个说法!否则,本官绝不善罢甘休!
”看来是打算走经济赔偿路线了。我翻了个白眼。“要钱没有,要命一条。
不过……”我话锋一转,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。“我这儿有一本账册,
记录了某人这些年挪用岳家军饷、收受贿赂、还有在青楼嫖娼不给钱的详细数据。
不知道赵大人有没有兴趣赎回去?”5这句话的威力,
不亚于在赵文宣的裤裆里塞了一颗点燃的炮仗。他整个人都弹了一下,眼睛瞪得像是铜铃,
死死地盯着我。“你……你说什么?”声音都变调了,像是被人掐住了脖子的公鸭。
“听不懂?那我展开讲讲。”我笑眯眯地靠在门框上,开始如数家珍。“天佑三年,
你进京赶考,拿了我爹五百两银子,转头就去了‘醉红楼’,点了头牌小桃红。
那晚你喝多了,还给人家写了首湿哒哒的情诗,落款是‘未来首辅’。
那诗写得那叫一个烂啊,我都替你脸红。”“天佑四年,你初入翰林,为了巴结上司,
送了一尊玉佛。那玉佛是你从我嫁妆里偷的,价值连城。结果呢,人家嫌弃是旧货,
转手就赏给了下人。”“还有天佑五年……”“够了!住口!你给我住口!
”赵文宣疯了一样扑过来,想要捂住我的嘴。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,他以为做得天衣无缝,
没想到全被我记在了小本本上。其实我根本没什么账册。这些都是上辈子他喝醉了酒,
自己吹牛逼告诉我的。但是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,他信了。看着他气急败坏扑过来的样子,
我眼底闪过一丝寒光。等的就是你先动手。就在他的手即将碰到我的瞬间,我动了。
侧身、抬腿、绊脚、推背。一套动作行云流水,一气呵成,
充分展示了我多年来对人体力学的深刻理解。“噗通!”赵文宣像一只断了翅膀的秃毛鸡,
重重地摔在了地上,脸正好砸在了那桶我还没来得及倒掉的泔水旁边。虽然没掉进去,
但那股子酸爽的味道,足够他回味三天了。“哎呀,赵大人,您这是干什么?行此大礼,
民女可受不起啊。”我故作惊讶地喊道,身体却连动都没动一下,完全没有要扶他的意思。
赵文宣趴在地上,半天没爬起来。周围的笑声更大了。堂堂京兆尹,当街扑街,
这绝对是明天京城的头条新闻。“姜……姜离……”他艰难地抬起头,满脸通红,
眼神怨毒得想要吃人。“你给我等着!此仇不报,我赵文宣誓不为人!”“好啊,我等着。
”我蹲下身,手里转着那把杀猪刀,刀尖在地上划出一道道刺耳的摩擦声。“不过,赵大人,
回去最好先查查你那个好妹妹。别回头被人卖了,还帮人家数钱呢。”我意味深长地笑了笑。
赵文宣愣了一下,眼神里闪过一丝疑惑。他多疑。这是他最大的弱点,也是我最好用的武器。
这颗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,迟早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,
把他们那个脆弱的利益同盟搞得支离破碎。赵文宣最后是被那两个衙役搀扶着走的。
走的时候一瘸一拐,背影萧瑟,充满了败家之犬的颓废美感。我站在店门口,目送他远去。
夕阳西下,残阳如血。我深吸了一口气,闻到了空气中弥漫着的、即将到来的暴风雨的味道。
真好闻。比这满屋子的生肉味,要好闻一千倍。游戏,才刚刚开始呢。
6赵文宣带着他的国家机器灰溜溜地撤退了,带走了他的官威,留下了一地鸡毛和一个传奇。
从第二天起,我的“姜记肉铺”迎来了业务上的井喷式增长。前来买肉的人民群众络绎不绝,
他们看我的眼神,已经不是在看一个普通的屠夫,
而是在瞻仰一位刚刚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女元帅。“老板娘,来半斤后腿肉,
要您昨天用来展示人体结构学那个部位的!”“姜元帅!给我来一根筒骨!
我儿子马上要考试了,我回去给他熬汤,沾沾您的文武双全之气!”我挥舞着杀猪刀,
在案板上下翻飞,感受着人民群众朴素而热烈的崇拜。我觉得我不是在卖肉,
我是在签售我的自传。每一刀下去,都是一个龙飞凤舞的签名。
就在我忙得像个即将过劳死的陀螺时,一个青衣书生站在了我的摊位前。
他不像别人那样咋咋呼呼,就那么安静地站着,手里拿着一把旧得掉漆的折扇,
脸上带着一种看破红尘的微笑。在这个充斥着荷尔蒙与猪下水味道的环境里,
他显得格外的……格格不入。像是掉进火锅底料里的一块薄荷糖。“公子,买肉吗?
”我头也不抬地问。“不,在下不买肉。”他的声音很好听,像山间清泉流过石头的声音,
干净清澈。“在下是来谈投资的。”我手里的刀顿了一下,终于抬起头看了他一眼。
这书生长得眉清目秀,就是脸色有点苍白,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。“投资?”我乐了,
“你看我这小破店,哪里值得您投资?难道你想入股我下个月的猪下水期货?
”书生摇了摇扇子,笑了。“姑娘说笑了。在下姓裴,单名一个寂字。
就住在这西市的巷子里。”“昨日姑娘一场‘自卫反击战’,打得是惊天动地,
在下佩服得五体投地。”我眯起眼睛。这人不简单。他把我打架斗殴的行为,
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,这说明他要么是个疯子,要么就是个懂行的。“所以呢?
”我把刀插在案板上,抱起胳膊,“裴公子究竟想投资什么?”裴寂收起扇子,
往前凑了一步,压低了声音。“在下想投资姑娘的复仇大业。”他看着我,
眼神亮得像是黑夜里的星星。“赵文宣不是个简单的角色,他的背后,牵扯着更大的人。
姑娘单枪匹马,虽然勇猛,但双拳难敌四手。而在下,恰好知道一些他们的秘密。
”我心里咯噔一下。这家伙,是来递投名状的?“你想要什么?”我问道。
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,更没有白送的情报。裴寂笑了笑,伸出两根手指。“第一,
我要赵文宣身败名裂。”“第二,我要他背后的那个人,付出代价。
”他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深不见底的恨意。看来,又是一个有故事的男同学。“成交。
”我伸出油腻腻的手。裴寂看了看我的手,又看了看自己干净修长的手指,犹豫了一秒,
还是握了上来。“那么,作为合作的诚意,”他在我手心里轻轻写了几个字,
“姑娘不妨去查一查,城东的‘济世堂’药铺。”我感受着手心里的笔画,眉毛一挑。
“济世堂”?那不是江柔她娘家开的药铺吗?7赵文宣的府邸。今天的气氛很压抑,
压抑得像是便秘了十天的病人的脸色。赵文宣坐在主位上,手里端着一杯茶,却迟迟没有喝。
他的脸色比茶水还要冷。地上跪着的,是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江柔。她的头发散乱,
衣服上还有没洗干净的污渍,看起来像是一朵被霜打过的蔫巴白菜。“老爷,
你要为妾身做主啊!那个贱人……她不仅打我,她还羞辱我!她是在打您的脸啊!
”江柔一边哭,一边偷偷抬眼看赵文宣的反应。以前,只要她这么一哭,
赵文宣就会心疼得把她搂进怀里好生安慰。但今天,赵文宣像是一尊石雕,一动不动。
他的脑子里,反复回响着姜离最后说的那句话。“回去最好先查查你那个好妹妹。
”那句话像一根毒刺,深深地扎进了他的心里。他本来不信。但是姜离那副笃定的样子,
让他不得不信。更何况,他这个人,天生就不相信任何人。“柔儿,”他终于开口了,
声音沙哑,“你再跟我说一遍,当年姜家的事,你真的一点都不知情?”江柔的哭声一滞,
身体不可察觉地僵硬了一下。“老爷,您怎么又问起这个了?当年我们不是说好了吗?
姜家通敌叛国,罪有应得,我们……我们都是被蒙蔽的啊。”她的回答滴水不漏,
和以前说过的一模一样。但赵文宣却从她的眼神里,看到了一丝闪躲。“是吗?
”赵文宣放下茶杯,缓缓站起身,走到她面前。“可是我记得,
当年姜将军通敌的那封‘罪证’,是从你爹的书房里搜出来的。”他的声音很轻,
却像一记重锤,砸在了江柔的心上。“那……那是姜离那个贱人栽赃陷害!是她想害我爹!
”江柔尖声叫道,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。“栽赃?”赵文宣冷笑一声,“可是我派人去查了。
当年你爹的一个老仆人招供了,说那封信,是你亲手交给你爹的。”轰!
江柔的脑子里像是炸开了一个惊雷。她不可置信地抬起头,
看着眼前这个曾经对她百般宠爱的男人。他的眼神里,没有了往日的温柔,
只剩下冰冷的审视和猜忌。“老爷……你……你不相信我?”她颤抖着伸出手,
想要去抓赵文宣的衣角。赵文宣却后退一步,躲开了。“我只相信证据。
”他冷冷地扔下一句话。“在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,你就在这个院子里好好待着,
哪儿也不许去。”说完,他转身就走,没有丝毫留恋。“老爷!老爷你听我解释!
不是那样的!是姜离!都是姜离那个贱人在挑拨离间!”江柔跪在地上,声嘶力竭地哭喊着。
但赵文宣的脚步,没有片刻的停留。房门被“砰”的一声关上,外面传来了落锁的声音。
江柔的哭喊声戛然而止。她瘫软在地,眼神里满是恐惧和绝望。她知道,自己的好日子,
到头了。一个坚固的堡垒,往往最先从内部开始腐烂。而我,只不过是往那墙缝里,
轻轻地吹了一口气而已。8赵文宣这个人,虽然人品烂到了地心,但脑子还是有的。
他很快就明白,跟我进行正面的物理对抗,他占不到任何便宜。所以,他决定跟我玩阴的。
他开始对我进行惨无人道的经济制裁。第一天,给我供货的张屠夫就没有来。我去他家一问,
他哭丧着脸告诉我,他家的猪圈被衙门给封了,说是他的猪没有办理“准生证”,
属于非法养殖。我当时就想笑。准生证?你咋不说猪没做核酸不让出圈呢?第二天,
我试图从别的屠户那里进货。但是所有人都像是躲瘟神一样躲着我。一打听才知道,
京兆尹衙门刚刚颁布了一条新规定,叫《关于规范京城鲜肉市场流通秩序的若干意见》。
里面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,核心思想就一个:谁敢卖肉给我姜离,谁就是和人民为敌,
和政府作对。第三天,我肉铺的房东也找上门来了。一个矮矮胖胖的中年男人,
平时见我跟见了亲妈一样热情,今天却一脸便秘的表情。“姜……姜姑娘,不是我不讲情面,
实在是……衙门说了,我这铺子违规建筑,要限期拆除。您看……您还是尽快搬走吧。
”我看着他闪烁的眼神,心里跟明镜似的。赵文宣这是釜底抽薪,打算从供应链到销售终端,
对我进行全方位的立体化打击。这战术,够狠,也够脏。肉铺里没有肉,就像军队没有子弹。
我坐在空荡荡的案板前,闻着空气中残留的肉腥味,第一次感到了一丝棘手。
这是一场非对称战争。他手里握着公权力,而我手里,只有一把杀猪刀。正规军打游击队,
确实不好打。连着三天没开张,周围的邻居看我的眼神都变了。从最初的崇拜,变成了同情,
最后变成了惋惜。“哎,这姜姑娘也是可怜,胳膊拧不过大腿啊。”“就是,得罪了官家,
哪有好果子吃。”我听着这些议论,心里却没有丝毫波澜。他们不懂。真正的猎人,
都是极具耐心的。在没有找到敌人致命弱点之前,暂时的蛰伏,是为了最后的雷霆一击。
就在第四天傍晚,我等的人,终于来了。裴寂还是那身青衣,慢悠悠地晃进我的店铺。
他看了看我空空如也的货架,又看了看我。“看来,敌人的第一轮空袭,很猛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