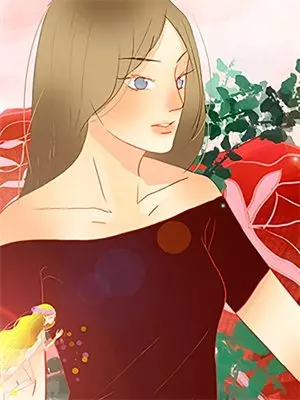
血从腰间断开的地方汩汩地往外冒时,无一郎忽然想起一件事。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,
久到他以为早就忘了。那时他大概四岁,也许五岁,记不清了。他在山道上摔了一跤,
膝盖磕在石头上,破了好大一块皮,血一下子涌出来。他吓坏了,坐在地上哇哇大哭。
哥哥从前面跑回来,蹲下来看他伤口,眉头皱得紧紧的。“别哭,”哥哥说,声音有点急,
“越哭越疼。”可他还是哭。哥哥就从怀里掏出块粗布手帕——洗得发白,
角上绣着朵歪歪扭扭的小花,是母亲绣的——按在他伤口上。血很快渗出来,把帕子染红了。
哥哥的手有点抖,但还是按得很稳。“忍一忍,”哥哥说,“忍一忍就不疼了。
”后来哥哥背他回家。他趴在哥哥背上,脸贴着哥哥的后颈,
能闻到哥哥身上汗味混着青草的味道。哥哥走得很慢,很稳,一步一步,怕颠着他。
夕阳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,在山道上晃晃悠悠的。那时候他觉得,哥哥的背真宽啊,
像能挡住全世界所有的风雨。现在呢?现在他躺在无限城冰冷的地板上,
血从腰间断口涌出来,比小时候膝盖上的伤口多得多,怎么堵都堵不住。
好像有人的手按在他的伤口上,用力得指节发白,但血还是从指缝间涌出来,温热的,
黏稠的,在地板上漫开。他看不见自己的血,但能感觉到。那种生命从身体里流失的感觉,
很缓慢,很清晰,像沙漏里的沙,一粒一粒,不紧不慢地往下漏。啊,这次哥哥不会来了。
这个念头浮上来时,很平静。就像知道天黑了该点灯,下雨了该收衣服那样平静。
哥哥早就死了,十一岁那年就死了,被鬼杀死了。现在轮到他了。也好。他想。至少这次,
不用一个人活着了。黑暗漫上来时,他听见有人在哭。是不死川先生吗?
那个总是凶巴巴、说话像吵架的风柱,居然也会哭吗?声音哑哑的,破碎的,混着血沫,
很难听。还有别的声音,远处打斗的声音,建筑崩塌的声音,木头断裂的声音。
但这些声音都越来越远,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棉被。只有血从身体里流走的声音是清晰的。
那种细微的、持续不断的汩汩声,像山涧的水,永远流不完。最后消失的是嗅觉。血腥味,
尘土味,还有……不死川先生身上的味道,汗味混着铁锈味。这些味道都淡了,散了,
像晨雾被太阳一晒,就没了。然后什么都没了。醒来时,先感觉到的是风。很轻很软的风,
拂过脸颊,像母亲的手。无一郎睁开眼,看见一片金黄——麦田,无边无际的麦田,
麦穗沉甸甸的,在风里轻轻晃动,沙沙作响。天空是洗过一样的蓝,干净得透明,
一丝云都没有。他坐起来。身下是松软的泥土,混着干草和阳光的味道。
低头看自己:鬼杀队的队服不见了,穿的是粗布的衣衫,洗得发白,袖口磨起了毛边,
针脚歪歪扭扭的,一看就是外行人缝的。腰还在,腿还在,左手也在。他举起左手看了看,
五指健全,没有伤,没有血。他掐了自己一把,会疼。不是梦。他站起来,动作很轻,
像怕惊动什么。麦子长到腰间,风过时麦穗蹭着手臂,痒痒的。远处有田埂,
土路被踩得发亮,在阳光下泛着浅浅的金色。田埂上坐着个人。海带般的头发,瘦瘦的肩膀,
穿着和他一样的粗布衣服。背对着他,一动不动,像座小小的雕像。无一郎的心跳停了。
他往前走,一步,两步。脚步很轻,但踩在泥土上还是有声音,轻微的噗嗤声。
走到离田埂还有几步远时,那人回过头来。时间真的停了。有一郎!是有一郎!!他的哥哥!
!!有一郎的脸,和记忆里一模一样。停留十一岁,还没完全长开,下巴尖尖的,眼睛很大,
看人的时候很专注,像要把人看穿。“发什么呆。”有一郎开口,
声音也是记忆里的那般稚嫩。是啊,他那时才十一岁啊。无一郎张了张嘴,发不出声音。
他往前走一步,这一步踩实了,土是温的,透过薄薄的草鞋底传来温度。再一步,
就到了田埂边。他盯着哥哥看,眼睛眨都不敢眨,怕一眨眼,这人就散了,
像晨雾被太阳一晒就没了。有一郎也看他,从上到下,看得很仔细。从乱糟糟的头发,
到额头,到眼睛,到鼻子,到嘴唇,到下巴,到肩膀,到手,到腰,到腿。一寸一寸地看,
像在确认什么。然后他叹了口气,那叹息很轻,混在麦浪的声音里几乎听不见。
他伸出手:“过来。”无一郎握住那只手。温暖的,真实的,掌心有茧——是劈柴留下的,
采药留下的,干活留下的。他握得很紧,紧到指节发白,指甲都嵌进哥哥手背的皮肤里。
“疼。”有一郎说,但没抽手。无一郎松开一点,但还是握着。他在田埂上坐下,挨着哥哥,
肩膀碰着肩膀。真实的触感,真实的温度,真实的重量——欸?我比哥哥还高了。
无一郎晃了下头,试图让自己冷静。“哥哥,你在。”他终于说出话,声音哑得厉害,
像很久没开口说话。“等你呢。”有一郎说,语气很平常,像在说“饭做好了”那样平常。
“等了多久?”“记不清了。”有一郎仰头看天,脖颈的线条很清晰,喉结微微滑动,
“这里的时间……不太一样。可能很久,也可能没多久。”无一郎也抬头。太阳挂在西边,
斜斜的,光线金黄,但不刺眼。确实,它好像就没动过,就那么挂着,像画上去的。
风吹过来,麦浪一层层荡开,金色的波纹一直推到天边。远处有山,青灰色的轮廓,淡淡的,
像用最淡的墨描上去的。“这里……”无一郎想问什么,又不知道从何问起。“交界处。
”有一郎接话,好像知道他要问什么,“还没到那边,也不在那边。
给……犹豫的人待的地方。”“哥哥在犹豫吗?”“等你。”有一郎侧过头看他,眼睛很亮,
“你太笨了,我怕你来了找不到我。”无一郎鼻子一酸。他低头,
看见自己和哥哥的手还握在一起。“我死了。”他说。“嗯。”“被腰斩的。上弦之壹,
黑死牟。”有一郎的手紧了一下,很细微的动作,但无一郎感觉到了。那只手抖了一下,
很轻的一下,然后握得更紧。“疼吗?”有一郎问,声音很轻。“当时疼。”无一郎老实说,
“后来就不疼了。像……像脱了件特别重的盔甲,一下子轻了。”有一郎没说话,
只是把他的手握得更紧些,像要把所有的温度都传过来。他们就这样坐着,看麦田,看天,
看云。云走得很慢,慢到几乎察觉不到它在动。有一郎开始哼歌,不成调的歌,
零零碎碎的旋律,无一郎记得——是母亲以前哄他们睡觉时哼的。“哥哥。”无一郎说。
“嗯?”“黑死牟……是我们的先祖。”有一郎停住了哼歌。他沉默了一会儿,
很长的一会儿,长到无一郎以为他不会回答了。“我知道。”他终于说,声音很低,
“我看见他了。从你进那个房间开始。”“哥哥看见了?”“看见了。”有一郎转过来,
看着他,“从他出现,到他说那些话,到你们战斗……我都看见了。你的左手被砍断,
你的身体被刺穿,你的腿被斩断,最后……腰被斩断。”无一郎看着哥哥的眼睛。
那双很深的眼睛里,有很深的痛苦,深得像井,望不到底。“哥哥一直都在看?”他问。
“嗯。”有一郎点头,“从你进鬼杀队开始。每一次训练,每一次受伤,每一次杀鬼。
你第一次用出霞之呼吸,你第一次参加会议,你和那个叫炭治郎的孩子一起吃饭,
你和那个小女孩一起歪头,你和那只丑丑的大头鬼一起战斗……我都看见了。
”无一郎想象那个画面——哥哥一个人,在这个时间静止的地方,远远地看着自己活着,
战斗,受伤,成长。看着自己从一个什么也不记得的孩子,变成能独当一柱的剑士。
看着自己离死亡越来越近,却什么也做不了。“对不起。”他声音发颤。“对不起什么?
”“让哥哥一个人……等这么久。看着那么多。”有一郎摇摇头,手从他手上松开,
轻轻摸了摸他的头。动作很轻,像怕碰碎什么。“你活得很好。”他说,声音很哑,
“比我能想象的还好。你成了柱,你保护了很多人,你……很了不起。”“可是我死了。
”“谁都会死。”有一郎说,“重要的是怎么活。你活得很耀眼,无一郎。像真正的霞,
虽然留不住,但谁看了都忘不掉。”眼泪终于掉下来。无一郎没忍住,也不想去忍。
他低着头,眼泪一颗颗砸在粗布裤子上,洇开深色的圆点,一个接一个。有一郎揽过他,
让他靠在自己肩上。无一郎闻到了熟悉的味道——阳光晒过的衣服的味道,
混着一点草叶的清气,还有很淡很淡的、属于哥哥的、说不清是什么但就是能认出来的味道。
哥哥,好温柔。他哭出声来。十四年来第一次这样哭,不是默默流泪,是真的哭出声,
像小时候摔疼了那样,不管不顾地哭。声音很难听,嘶哑的,破碎的,混着鼻涕和眼泪。
有一郎什么都没说,只是轻轻拍他的背,一下,一下。力道很轻,像在哄小婴儿。
麦田在风里沙沙响,像在附和这哭声。远处的山静默着,天空蓝得透明。哭了很久,
眼泪好像流干了。眼睛肿了,鼻子塞了,喉咙也哑了。无一郎坐直,用袖子擦脸,
袖子湿了一大片,黏黏地贴在脸上。“丑。”有一郎说。“你才丑。”无一郎回嘴,
声音还带着浓重的鼻音。有一郎笑了,那笑容很浅,但很真实。他站起身,
拍了拍裤子上的土,伸手拉无一郎:“走,带你去看看。”他们沿着田埂走。路不宽,
刚好容两个人并肩。有一郎走在靠田的一侧,无一郎走在靠外的一侧。小时候也是这样,
出门时哥哥总让他走里面,说外面危险。“我们去哪?”无一郎问。“回家。”有一郎说。
家。无一郎心里动了动。他跟着哥哥,走过长长的田埂。麦田好像没有尽头,
金色的海洋在风里起伏。远处有树林,深绿色的,密密匝匝的,像一堵墙。走进林子,
光线暗下来。树叶层层叠叠,把阳光滤成碎金,洒在地上。地上积着厚厚的落叶,
踩上去软软的,发出轻微的咔嚓声。空气里有潮湿的泥土味和腐烂的叶子味。
无一郎跟在哥哥身后,看哥哥的背影。十一岁的背影,瘦且单薄。
手臂在粗布衣服下随着动作微微起伏,像蝴蝶的翅膀。“哥哥。”他叫。“嗯?
”“你在这里……吃什么?睡哪里?”“有吃的。”有一郎回头看了他一眼,
眼睛在树荫里很亮,“果子,蘑菇,有时候能抓到鱼。睡的话……我搭了个屋子。”“屋子?
”“嗯。”有一郎转回头,继续往前走,“反正时间多,慢慢弄。总得有个地方待。
”林子深处,果然有间小屋。木头搭的,不大,但很结实。屋顶铺着厚厚的茅草,
被晒成了金黄色。屋檐下挂着风铃——用细竹管和贝壳做的,风一吹,叮叮当当,声音很脆,
在安静的林子里格外清晰。门前有棵树,老杉树,枝叶茂密,投下一大片阴凉。树干很粗,
要两个人才能合抱,树皮粗糙,裂开深深的纹路。无一郎站在那儿,看了很久。
这棵树……和老家门前那棵好像。小时候,他总喜欢爬到那棵树上,坐在最高的枝桠上,
看远处的山,看天上的云。哥哥在下面喊他下来,说危险,他不听。有一次真的摔下来了,
哥哥接住了他,两个人都摔在地上,疼得龇牙咧嘴。“哥哥一个人搭的吗?”他问。“嗯。
”“花了多久呀?”“不知道。”有一郎推开门,木门发出吱呀的声音,
“这里的时间……算不清。可能很久,也可能没多久。”屋里很干净,
干净得不像一个人住的地方。两张草席铺成床,靠墙放着,隔着一臂的距离。一张矮桌,
很旧了,桌腿有修补过的痕迹。几个坐垫,布面磨得发白。墙角堆着柴火,码得整整齐齐,
像用尺子量过。灶台在另一边,石头垒的,上面架着一口铁锅,锅里煮着什么,冒着热气,
白色的水汽袅袅上升。无一郎走进去,环顾四周。墙上挂着斗笠和蓑衣,
窗台上摆着几个木雕的小玩意儿——粗糙但能看出形状:一只鸟,翅膀张着,
像要飞;一条鱼,尾巴翘着,像在游;一朵花,花瓣层层叠叠。“哥哥雕的吗?
”他指着那些。“嗯。闲着没事。”有一郎走到灶台边,掀开锅盖,热气扑出来,
模糊了他的脸,“吃山芋吧。你以前爱吃。”确实是山芋,煮得软软的,皮都裂开了,
露出里面金黄的内瓤。盛在粗陶碗里,碗边有个小缺口,但不影响使用。他们坐在门槛上吃,
一人一碗。无一郎咬了一口,甜的,糯的,热乎乎地从喉咙滑下去,一直暖到胃里。
“好好吃。”无一郎笑了。“慢点,烫。”有一郎说,自己也吃了一口,吹了吹气。
夕阳斜斜地照过来,把他们的影子拉长,投在地上。影子挨着影子,头靠着头,
分不清谁是谁。“哥哥。”无一郎吃着,忽然说。“嗯?”“黑死牟死前……说了些话。
”有一郎的手顿了顿,勺子停在半空。然后他继续吃,但吃得很慢,像在等什么。
“他说他记得自己的名字。”无一郎看着碗里的山芋,“继国岩胜。
他说……他弟弟是继国缘壹,那个天生就会呼吸法的人。他一直追,一直追,追了四百年,
还是没追上。”有一郎沉默地听着,勺子轻轻搅动碗里的山芋。风从林子里吹过来,
带着树叶的沙沙声,还有远处鸟的鸣叫。“你怎么想?”有一郎问。
“我……”无一郎想了想,“我觉得他很可怜。但不可原谅。他杀了太多人了。”“嗯。
”有一郎点头,“可怜和可恨,有时候是一起的。”他吃完最后一口山芋,放下碗,
看着远处渐渐暗下来的天色。“我有好多话想对你说,我们边走边聊。”“嗯,走!
”“我看了你这么久。”他边走边说,声音很轻,“看着你从什么都不记得,
到慢慢想起一些事,到成为柱,到最后……死。我看着你受伤,看着你哭,看着你笑。
我看着你和那些孩子一起训练,看着你和他们吵架又和好。我看着你越来越强,
也越来越像……一个真正的人。”无一郎看向他。哥哥的侧脸在暮色里很柔和,睫毛很长,
在下眼睑投出小小的阴影。“你本来可以当个普通人。”有一郎继续说,“结婚,生子,
老死。不用拿刀,不用见血,不用在十四岁就死。但我知道……那样的话,你就不是你了。
”他转过头,看着无一郎,眼睛很亮,像有星星在里面。“你是时透无一郎。霞柱。
我的弟弟。你选了最难的路,走了最远的路,然后……回来了。”无一郎鼻子又酸了。
他低下头,看着自己的手。这双手握过刀,杀过鬼,救过人。现在干干净净的,没有血,
像一个真正十四岁孩子的手。“我开启斑纹了。”他说。“我知道。”“还开启了赫刀。
”无一郎抬起手,看自己的手掌,“就在最后,腰被斩断的时候。
我想着……不能就这么死了,得再做点什么。然后刀就变红了。
”有一郎侧过头看他:“疼吗?”“不记得了。”无一郎老实说,
“那时候已经感觉不到疼了。就想着……要困住他,给行冥先生和不死川先生创造机会。
”“你做到了。”“嗯。”无一郎点头,“黑死牟死了。我们赢了。”“你们赢了。
”有一郎重复,声音很轻,像怕惊动什么。“是我们赢了!哥哥”夕阳完全沉下去了,
天色从橘红变成深紫,再变成靛青。星星一颗一颗亮起来,先是几颗特别亮的,
像钉在天幕上的银钉,然后是越来越多,密密麻麻的,撒了一天,像谁打翻了一袋珍珠。
林子里有萤火虫飞出来。绿莹莹的光点,在草丛间飘浮,忽明忽暗,像碎掉的星星掉下来了,
在地上挣扎着发光。“哥哥。”无一郎在星光下说。“嗯?”“我其实……有点怕。
”“怕什么?”“怕黑死牟说的那些。”无一郎低头看着自己的手,“他说我是他的后代,
说我们流着一样的血。我怕……怕我以后也会变成那样。为了变强,什么都不管了。
”有一郎伸手,揽过他的肩,让他靠着自己。哥哥的肩膀不宽,但很结实,靠着很安心。
“你不会。”有一郎说,声音很肯定,像在陈述一个事实,“因为你是我弟弟。
”无一郎抬头看他。“我们流着一样的血,你和我。”有一郎看着他,眼睛在星光下很亮,
像两潭深水,“我胆小,自私,只想让你当个普通人,平平安安过一辈子。你勇敢,坚强,
选了最难的路,去保护更多的人。我们流着一样的血,但我们是不同的人。
”无一郎鼻子又酸了。他低下头,额头抵着哥哥的肩膀。哥哥的衣服很薄,
能感觉到下面的骨头,硬硬的,但很温暖。“而且,”有一郎继续说,手轻轻拍他的背,
像小时候哄他睡觉那样,“你已经证明了自己。你用那条命,做了最了不起的事。
你不用再证明什么了,无一郎。”夜风很凉,从林子里吹过来,带着露水和泥土的气息。
但哥哥的肩膀很暖,像一个小小的火炉,驱散了所有的寒意。“我想父亲母亲了。
”他小声说。“他们也在等我们。”有一郎说。“我们能见到他们吗?”“能。
”“什么时候?”“等你想去的时候。”有一郎松开他,看着他的眼睛,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