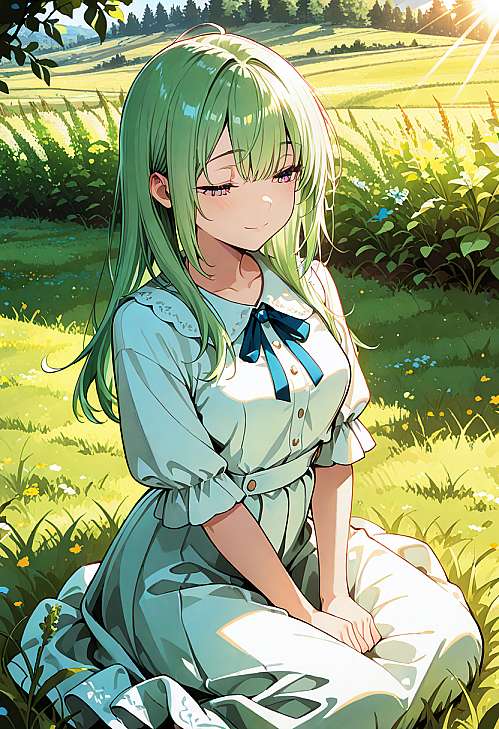1 血色重生沈清辞在冰冷的余痛中睁开双眼。窗外天色将明未明,
床帐上熟悉的缠枝莲纹在晨光中朦胧可见——这是她的闺房,镇国公府的闺房。
沈清辞缓缓摊开双手,十指完好。可指尖为何还在灼烧?
那被李瑾瑜一剑削断三指的痛楚怎么还在?我不是死了吗?她猛地坐起身,
铜镜里映出一张苍白却年轻的脸。明日……明日就是她与李瑾瑜定下婚约的大典之日。
种种记忆轰然涌入:李瑾瑜看似温文尔雅,
大婚后却动辄鞭笞;庶妹沈若薇总挂着善解人意的笑,一次次将她推向深渊;最后那个雪夜,
匕首刺入心口的冰凉,她甚至听见自己肋骨断裂的声音……“好。”她低语,
唇角浮起一丝极冷的弧度,“都回来得正好。”窗外的晨光渐亮,
将她眼底的寒意照得清明如刃。沈清辞眼底最后一丝温婉褪尽,淬为冰刃。恰在此时,
门被轻轻推开。沈若薇一身素色衣裙,端着青瓷碗袅袅而入。
她眉间拢着一缕恰到好处的忧色,声音柔得像春日柳絮:“姐姐明日便要定亲了,
妹妹特意熬了安神汤,愿姐姐今夜好眠。”那碗汤热气袅袅,
氤氲着寻常草药难以分辨的、一丝极淡的异香。前世,正是这碗“好意”,
悄无声息地蚀空了她的气血,让她在婚后成了无力挣脱的困兽。沈清辞心口冷笑,
面上却不显。她伸手去接,指尖触及碗壁的刹那,手腕“不经意”地一倾——“哎呀!
”温热的汤药尽数泼洒在沈若薇月白的裙裾上,顿时污浊一片。“妹妹怎么这么不小心?
”沈清辞抢先开口,语气里满是无辜的讶异,她伸手扶住惊呆了的沈若薇,指尖却暗中用力,
不容对方挣脱。“走路都这样不稳。汤洒了倒是小事,只是可惜了妹妹这身好衣裳。
”她微微倾身,在沈若薇耳边压低了声音,气息轻得像叹息,字字却清晰如针,
“况且……这汤里的药材气味,似乎格外特别呢。”沈若薇浑身一僵,
脸上刻意维持的柔弱几乎瞬间碎裂。她瞳孔骤缩,猛地看向沈清辞,
撞入一双深不见底、了无波澜的眼眸。那眼里没有往日的温顺信赖,只有一片冰冷的洞悉。
“姐、姐姐何出此言?这只是寻常的安神汤……”沈若薇慌忙辩解,声音却不由自主地发颤。
“寻常?”沈清辞轻轻打断,目光扫过地上狼藉的汤渍,又缓缓移回沈若薇惨白的脸上,
“妹妹博闻强识,不如告诉我,是哪几味‘寻常’药材,能混出这般独特的辛涩之气?
倒像……混了些不该出现在闺阁汤药里的东西。”她步步向前,沈若薇便下意识地步步后退,
直到脊背抵上冰凉的门框,退无可退。“我……我不懂姐姐在说什么!”沈若薇语无伦次,
额角渗出细密冷汗,“许是、许是熬药时奴婢不小心……”“妹妹的贴身丫鬟,
自然是极稳妥的。”沈清辞截住她的话头,唇角勾起一丝极淡的弧度,却无半分暖意,
“罢了,衣裙污了,妹妹还是快些回去更衣吧。仔细……着了凉。”沈若薇如蒙大赦,
又似被无形的手扼住咽喉,再也说不出一个字,只能仓皇敛起破碎的神情,
几乎是踉跄着夺门而出。沈清辞站在原地,垂眸看着地上渐渐冷却的污渍,
眼底最后一点虚幻的温度也消散殆尽。这才只是开始。夜色如墨,镇国公府书房却灯火通明。
沈清辞直挺挺地跪在冷硬的地面上,面前是面色凝重的父亲沈惊鸿,
与须发微霜、目光如电的外祖父柳渊。“女儿恳请父亲、外祖父,”她抬起脸,泪痕未干,
眼中却是一片破釜沉舟的决绝,“明日定亲大典,必须取消。李瑾瑜……绝非良人。
”沈惊鸿眉头紧锁:“清辞,此话从何说起?雍王仪表堂堂,才华出众,
京中多少人家求而不得……”“那是伪装!”沈清辞打断父亲,声音因激动而微颤,
却又异常清晰,“女儿暗中留意多时,亲眼见他于无人处鞭笞仆役,
手段狠辣;听闻他狎玩优伶,性情暴戾无常。此等表里不一、残忍成性之人,
女儿宁死不愿嫁!”柳渊一直沉默审视着外孙女,此刻缓缓开口,声音沉稳如古钟:“清辞,
你可知悔婚一事,关乎两家颜面,更可能招来皇室不满?你……可有实证?
”“辞儿愿以性命起誓,所言绝非虚妄!”沈清辞重重叩首,额头触及冰冷地面,
“女儿并非一时意气。这些时日,夜不能寐,反复思量,唯有此路可走。
父亲、外祖父素来疼我,难道忍心看我跳入火坑,一生凄楚?”她抬起泪眼,
目光在两位至亲脸上哀恳逡巡:“我不求立刻公之于众损他名声,只求明日大典不成。
事后李家若有任何责难,女儿一力承担,绝不敢连累家门!
”看着自幼宠爱、从未如此激烈反抗的孙女/女儿这般模样,沈惊鸿与柳渊对视一眼,
皆看到对方眼中的震动与挣扎。空气中沉默压得人喘不过气。良久,柳渊长长叹了口气,
似苍老了几分。他扶起沈清辞,粗糙的手掌拍了拍她冰凉的手背。“罢,罢。
”沈惊鸿也终于沉重地点了头,眼神复杂。沈清辞紧绷的心弦骤然一松,几乎软倒,
又被外祖父稳稳扶住。她垂下眼帘,掩住眸底翻涌的滔天巨浪。第一步,成了。接下来,
该轮到那些欠她命债的人,好好品尝她亲手奉上的“滋味”了。窗外夜色浓稠如化不开的墨,
而她的眼底,却燃起一抹幽冷的焰。2 惊世骇俗第二日,定亲大典。
皇室贵胄、文武重臣齐聚雍王府,李瑾瑜身着亲王礼服,眉目含笑,立于高台之上,
只等他的准王妃款款而来。然而,当沈清辞出现时,满堂喧哗霎时冻结。
她未着定亲礼制的月白吉服,反而一身正红长裙,裙摆迤逦,似泼洒开的烈烈鲜血,
直直撞入每个人眼底。她一步步走上台阶,步履沉稳,
在无数惊愕的目光与李瑾瑜骤然僵住的笑容前,站定。没有叩拜,没有婉辞。她抬手,
自袖中抽出那卷金线绣边的婚书,在死寂的大殿里,清晰无误地、缓缓地,将其撕成两半。
裂帛之声,刺耳至极。“臣女沈清辞,”她抬首,声音清越如玉石相击,穿透殿宇,“今日,
愿以死拒婚!”满场哗然如沸水炸开。“沈清辞!你疯了不成!
”李瑾瑜脸上的得意瞬间碎裂,化为暴怒的狰狞,他上前一步,厉声斥道,
“众目睽睽之下毁约背信,水性杨花,不知廉耻!镇国公府便是这般教养女儿?”就在这时,
沈若薇从人群中急急步出,眼中适时蓄起泪光,柔弱无骨般轻扯李瑾瑜的衣袖,
声音带着恰到好处的哽咽:“瑾瑜哥哥息怒……姐姐、姐姐许是近日心神不宁,一时糊涂了。
您千万别气坏了身子,再好好劝劝姐姐,她定会回心转意的……”字字体贴,
句句都在将“任性妄为”、“不识大体”的罪名,无声钉在沈清辞背上。沈清辞看着她表演,
忽地轻笑一声。那笑声不大,却冷冽如冰锥,瞬间压过了低语。她向前一步,目光如刃,
掠过脸色铁青的李瑾瑜,最终定格在沈若薇瞬间发白的脸上。“妹妹果然是解语花,
时时不忘为雍王殿下分忧。”她语调平缓,却字字清晰,“只是不知,昨日亥时三刻,
妹妹自后角门潜入雍王府,与殿下在偏厅‘私会’长达一个时辰,
又是在‘劝解’殿下些什么?”轰——一句话,如惊雷炸响,将整个大殿劈入死寂。
李瑾瑜与沈若薇的脸色瞬间惨白如纸,眼底是无法掩饰的惊恐。“你、你血口喷人!
”沈若薇尖声否认,声音却抖得不成样子。李瑾瑜亦急怒攻心:“放肆!沈清辞,
你竟敢污蔑亲王与贵女清誉!”“污蔑?”沈清辞眉梢微挑,不疾不徐,
“那不如请殿下与妹妹说说,亥时三刻,你们各自身在何处?殿下府上西侧偏厅临水,
昨日雨后地滑,妹妹鞋底沾的独特青苔,可还留着?殿下偏厅用的松烟墨里,掺了西域冰片,
气味特殊,妹妹袖口沾染的气息,此刻可散尽了?”她并无实证,
所言却时间、地点、细节俱全,丝丝入扣,直指要害。两人越是否认,越是慌乱,
落在众人眼中便越是可疑。窃窃私语声已变成震惊的议论,无数道目光如针,
刺向台上那对骤然失措的男女。就在这风声鹤唳、局面将崩未崩之际,
殿外忽然传来内侍悠长尖细的通传:“陛下驾到——”本为见证幼弟定亲而来的皇帝李曜,
身着常服,步入大殿。他的目光掠过狼藉的婚书碎片、面无人色的李瑾瑜与沈若薇,最终,
沉沉落在了那一身红衣、脊背挺直的沈清辞身上。那双深邃的帝王眼眸里,
极快地掠过一丝复杂的微光——惊诧,忧色,
以及一抹难以察觉的、对她如此狠绝反击的深沉赞许。沈清辞迎着他的目光,
毫不犹豫地转身,一步步走到御阶之前,屈膝跪倒,以额触地。再抬头时,
脸上已无半分方才的冷厉锋芒,只剩下一片玉石俱焚般的平静决绝。“臣女自知今日所为,
罪同欺君,祸连家门。”她声音朗朗,回荡在鸦雀无声的大殿,“然雍王非臣女良人,
臣女宁死不从。为全陛下天恩,为护沈氏满门,臣女斗胆——”她顿了一顿,
在所有人难以置信的屏息中,清晰吐字:“臣女愿入宫侍奉陛下,以全君臣之义,
以安家族之心!”死寂。绝对的死寂。当众撕毁与亲王的婚约,转而自请入宫为妃?
这已非惊世骇俗,简直是离经叛道,将皇室与世家颜面一同掷于地上!李曜瞳孔骤然收缩,
凝视着下方跪得笔直的女子。她红衣似火,眼眸如星,在滔天巨浪的中心,
竟有一种孤注一掷的、夺人心魄的烈性。高台之上,一直静观其变的太上皇李弘,
几不可察地,对着皇帝的方向,轻轻颔首。李曜收回目光,薄唇微抿。片刻沉寂,恍若隔世。
终于,他低沉而威严的声音响起,带着不容置疑的定鼎之力:“准奏。”两个字,
压下所有即将爆发的喧哗与质疑。“镇国公嫡女沈清辞,贤德明理,贞静端方。
着即册立为后,三日后,行大婚之礼。”旨意既下,乾坤已定。李瑾瑜僵立原地,面如死灰。
沈若薇踉跄一步,几乎软倒。沈清辞缓缓闭眼,复又睁开,眼底最后一丝波澜归于深寂。
她对着御座,深深叩首:“臣女,谢陛下隆恩。”红裙委地,如绽开的业火红莲。
3 入宫大婚三日后,镇国公嫡女沈清辞以皇后之礼,自正阳门入宫。銮仪煊赫,凤冠霞帔,
红妆迤逦过宫墙。朝野上下暗流汹涌,谁也未料,那场震惊京华的拒婚风波,
竟以此等石破天惊的方式收场——拒嫁亲王,直入中宫。镇国公府内,
沈谦与其母王氏气急败坏,砸了满屋瓷器。
他们精心筹谋、欲借沈清婚事攀附雍王李瑾瑜的青云路,尚未起步,便被她亲手斩断,
反将她自己送上了那至高却也至险的凤座。慈宁宫中,周太后撂下茶盏,
清脆的磕碰声在寂静殿内格外刺耳。
她保养得宜的脸上阴云密布:“沈家……未免太过得意了。” 沈氏门第煊赫,
如今嫡女又为皇后,外戚之势,已然让她感到了威胁。红烛高灼,映得坤宁宫寝殿满室温融。
龙凤喜帐上,金线绣出的百子千孙图在光影里微微浮动。沈清辞已卸去沉重的凤冠翟衣,
只着一身柔软的正红寝衣,坐在梳妆台前。镜中人眉眼如画,
却笼着一层挥之不去的疲惫与疏冷。青黛正为她梳理长发,
殿外传来通传:“陛下驾到——”殿门开合,李曜走了进来。他也换下了大婚礼服,
一身墨蓝色常服,身姿挺拔。他挥手屏退宫人,殿内只剩他们二人。他没有立刻走近,
而是在几步外停下,目光落在她映在镜中的侧脸上,那眼神很深,仿佛在确认什么,
又像是透过此刻,看着久远的过去。“终于,”他先开口,声音比平日低沉,
带着一丝几不可察的叹息,“你还是到了朕的身边。”这话语含义模糊,亲昵得突兀。
沈清辞心头一紧,起身规规矩矩地行礼:“陛下。”姿态是完美的恭敬,
却竖起了一道无形的墙。李曜似乎看穿了她的戒备,他缓步走近,却没有更进一步,
而是转向妆台上那支被她随手搁置的、不甚起眼的素银簪子。簪头是一朵简单的木兰花苞。
他拿起那支簪子,指尖轻轻摩挲过冰凉的花瓣。“这簪子,你倒还留着。”他语气平淡,
听不出情绪。沈清辞猛地抬眼,惊疑不定地看向他手中那支簪子。这是三年前,
她在西山断涧边“救”了那个从马背上摔下、扭伤了脚踝的“锦衣公子”后,
对方赠予她的谢礼。彼时她刚惊马救人,自己也狼狈不堪,对方却不顾伤痛,
从怀中取出这枚简单却精致的簪子,亲手为她拢好散乱的鬓发。“物归原主,
姑娘的救命之恩,他日必报。”那人声音温和,带着笑意,因疼痛而略显沙哑。
她当时只觉这公子气度不凡,却不曾细想。后来,她将那惊鸿一瞥的侧影与温润嗓音,
模糊地投射在了当时在京中风评尚可、同样气质温文的李瑾瑜身上。
“陛下……”沈清辞的声音有些发干,一个荒谬又令人心惊的猜测浮上心头,
“这簪子……是陛下所赠?”李曜转过身,面对她,烛光在他深邃的眼眸中跳跃。“三年前,
西山断涧,你救的不是什么迷路的世家公子。”他看着她骤然睁大的眼睛,一字一句道,
“是微服巡猎、不慎坠马扭伤脚踝的当朝太子,李曜。
”轰——仿佛有惊雷在沈清辞脑中炸开。那些尘封的细节瞬间串联:那日他虽衣着简朴,
盖不住的雍容气度、还有随后迅速出现又悄无声息处理现场的“家仆”……她怎么会那么蠢,
竟将这份恩情,错记在了李瑾瑜头上!而李瑾瑜,竟也从未否认,甚至可能顺水推舟,
利用了她的这份“误会”!前世种种模糊的关系,在这一刻被猛地照亮。
为何李瑾瑜起初对她还有几分表面客气,后来才越发暴戾?
巨大的荒谬感和被愚弄的愤怒席卷了她,让她脸色微微发白。
李曜将她的震惊与恍然尽收眼底。他放下簪子,走到她面前,
距离近到她能看清他眼中自己的倒影,以及那里面深藏的、复杂难言的情绪。
“朕找了你很久。”他低声说,不再是帝王的口吻,更像一个陈述往事的普通人,
“那日之后,朕被紧急护送回宫,待伤愈后再派人去寻,只知是镇国公府的小姐,
却不知是哪一位。等朕终于查明,你已……与瑾瑜定了亲。”他的声音里有一丝极淡的遗憾,
却并无责备。“朕看着你走向他,以为那或许是你自己的选择。”李曜的目光沉静地锁住她,
“直到你在定亲大典上,撕了婚书,一身红衣走到朕面前。那一刻朕才明白,
你或许从未真正看清过你要嫁的是谁,
也从未……真正得到过你当年冒险救下之人应给的庇护。”他伸出手,
不是象征性的帝后牵手,而是掌心向上,一个全然坦诚的邀请姿态。“现在,朕就在这里。
”他的声音低沉而坚定,“不是当年那个需要你援手、却无力立刻回报的伤者,
而是有能力护你一生安稳的帝王。沈清辞,你当年救下的那条命,朕如今,连同这颗心,
一并还给你,也一并交托给你。你可愿意……真正走到朕身边来?”不是施舍后位,
不是权衡联盟,而是基于一段被时光掩埋、却从未被遗忘的旧缘,
一次迟到却无比郑重的“相认”与“交付”。沈清辞看着眼前的手,又抬头看他。
烛光在他眼中映出温暖而笃定的光。前世冰冷的绝望,
与此刻汹涌而来的、错位多年的真相与暖意交织碰撞,让她眼眶骤然酸涩。她缓缓地,
将自己微凉的手放入他温暖干燥的掌心。这一次,不再是权衡利弊后的选择,
而是跨越了误解与时光,真正触碰到了可以依靠的彼岸。“原来……是陛下。”她声音微哑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