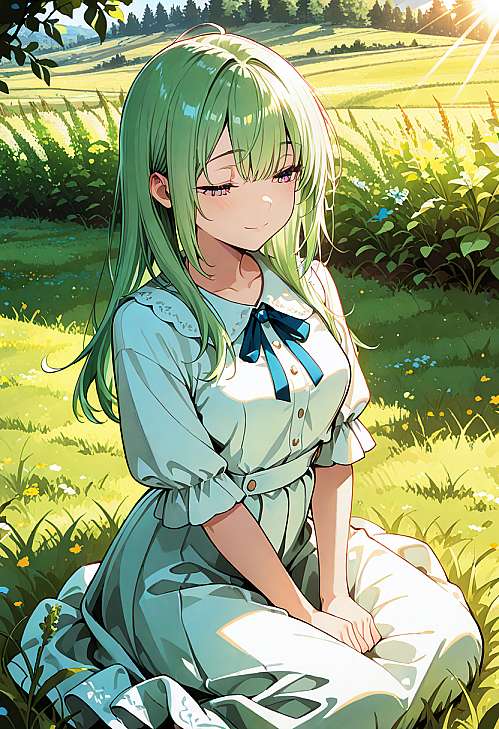冰得扎骨的皂角水猛地呛进鼻腔时,我还握着现代写字楼的工牌——指缝间残留的咖啡涩味,
和指尖搓着的粗布糙感撞得人发疼。抬眼是斑驳发潮的青石板,耳边是院角婢女的呵斥,
低头才看清,自己正蹲在柴房门口,搓着一盆沾着泥污的靴子,
我穿成了那本古代复仇小说里,连炮灰都算不上的无名洗脚婢。最初的日子,
我是凭着一股疯劲撑着的。撞过后院老槐树,
额头撞出青紫也不肯停;深夜裹着打补丁的薄衣,对着缺角的月亮絮絮叨叨念童谣,
盼着下一秒就能跌回出租屋的软床;甚至试过模仿小说里的情节,对着井口许愿。
可日子磨得人没了棱角,掌心的茧子厚得能磨破粗布,每天搓洗的靴子堆得比人高,
汗味混着皂角味浸得人发馊,管事嬷嬷的呵斥像鞭子似的抽在耳边,那些拼命想回去的尝试,
终究成了深宅里无人过问的笑话。希望是被冷水一点点浇灭的。我终于认了命,
把现代的骄傲折得严严实实,藏进粗布衣裳的褶皱里。学着低眉顺眼地回话,
学着手脚麻利地搓洗,学着在被刁难时默默忍下——不求别的,
只求能在后院这方寸犄角旮旯里,做个无人注意的影子,安安稳稳熬过这暗无天日的日子。
夜里搓完最后一盆靴子,坐在柴房门口吹着微凉的晚风,
我忽然想起这本穿越过来的小说的大体情节。我看过这本古代复仇文,只是当时看得潦草,
跳着翻完,许多细节记不清了,但核心的脉络,却渐渐在脑海里清晰起来。这府里,
是永安侯府,而小说的主角,是永安侯的嫡女。她本该是金尊玉贵的小姐,
却遭遇横祸——她的生母,永安侯的正妻,被侯府的柳姨娘暗中下了毒,
悄无声息地没了性命。而后,柳姨娘又设计陷害,将嫡女贬去了偏远的庄子,
让她在那里受尽磋磨,苟延残喘。听说在庄子里,欺负她的李嬷嬷一时嘴漏,
无意间说出了她母亲惨死的真相,那嫡女才幡然醒悟,从此卧薪尝胆,后来终于寻得机会,
重新回到了这永安侯府,一步步布局,向柳姨娘,向所有害过她和她母亲的人,展开了复仇。
那时只当是寻常的复仇爽文,看过便忘,没曾想,如今我竟真的置身于这本小说里,
成了最不起眼的尘埃。张嬷嬷是这深宅里唯一的光。她头发白得像落了层霜,
手脚却依旧利落,总能在我搓得指尖发麻、眼前发黑时,悄悄塞来一个温热的窝头,
还带着她怀里的体温;管事嬷嬷罚我跪雪时,她会借着扫雪的由头,
悄悄给我递来一块暖手的炭火,低声说“孩子,忍忍就过去了”。她的小孙女小翠,
是生来就被拴在府里的家生子,和我一起做最粗重的活,幼时一场高烧,府里不肯请大夫,
硬生生烧哑了她的嗓子,从此只剩怯生生的眼神,和急得发红时,手脚并用地比划。
那夜的雨,下得格外狠。后院的破屋漏得厉害,雨丝顺着房梁滴在稻草堆上,
砸出小小的泥坑,寒气像蛇似的钻进衣缝,冻得人牙齿打颤。我被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惊醒,
转头就看见张嬷嬷蜷缩在稻草堆里,脸色烧得像燃着的火炭,呼吸微弱得只剩一丝气音,
像风中随时会熄灭的烛火。我慌得赤着脚就冲出去找管事,冰冷的青石板扎得脚底生疼,
可管事只斜睨着我,啐了一口“贱奴也配烦主子?死个老奴罢了,
省得浪费粮食”;我想偷偷翻府墙,可青砖墙上的碎玻璃划破了手掌,
守卫的呵斥声在巷口响起——我们这样的奴隶,连求一条活路的资格,都没有。
我只能端来井里的冷水,一遍遍擦拭她滚烫的额头,井水冰得我指尖发麻,
却怎么也捂不热她的体温。她的手死死攥着我,指节泛白,
喉咙里断断续续地滚出“小翠”两个字,浑浊的眼睛里,只剩对孙女的牵挂。
我眼睁睁看着她的呼吸越来越轻,看着那点微弱的火光一点点熄灭,
看着她的体温从指腹的温热,慢慢褪成凉,再到冰得刺骨——那一刻,连雨声都仿佛停了,
只剩我自己的心跳,沉重得快要撞碎胸膛。小翠跪在一旁,浑身抖得像风中的枯叶,
双手死死抓着张嬷嬷的衣袖,指甲几乎嵌进布纹里。她张着嘴,
喉咙里只发出细碎的、破碎的气音,像被掐住脖子的小兽,眼泪砸在张嬷嬷冰冷的手上,
又溅到我的手背上,烫得发疼。我把她紧紧抱在怀里,感受着她单薄的肩膀剧烈颤抖,
看着张嬷嬷毫无血色的脸庞,心里那点“安稳活着”的念想,像被雨水泡过的纸,
“哗啦”一声,碎得彻底。原来这深宅大院,从来就没有“安稳”二字。
我们是任人践踏的蝼蚁,是可以随意丢弃的草芥,没有身份,没有权力,
连守护一个身边人、留住一条卑微的性命,都做不到。雨还在下,
皂角的涩味混着张嬷嬷平时攒下的野草药香,再裹着雨水的湿冷,钻进鼻腔,
呛得人眼眶发酸——那味道,成了刻在我骨子里的疤,提醒着我卑微的绝望。
我轻轻拍着小翠的背,指尖还残留着张嬷嬷冰冷的温度,怀里的颤抖让我瞬间清醒。
我咬着唇,直到尝到血腥味,才压下喉咙里的哽咽,
心里第一次燃起了滚烫的执念——我不能再浑浑噩噩,不能再任人宰割。我要往上爬,
哪怕前路满是荆棘,哪怕要踩着泥泞、忍着伤痛,我也要站到能护住自己、护住小翠的高度。
我要让我们,再也不用眼睁睁看着亲人离去,再也不用活得像尘埃一样,任人践踏。
可清醒之后,我又陷入了茫然——我一个无依无靠、连人身自由都没有的洗脚婢,无权无势,
又凭什么往上爬?这侯府深似海,到处都是趋炎附势之徒,没有靠山,哪怕拼尽全力,
也只会被碾得粉身碎骨。思来想去,我不得不承认一个残酷的事实:在这男尊女卑的侯府里,
我想往上走,想护住小翠,唯一的捷径,便是依靠男人。我拼命回想小说里的情节,
侯府之中,只有一位公子,便是柳姨娘的亲生儿子苏承轩。柳姨娘不过是个妾室,
却能在侯府里横着走,无人敢轻易招惹,究其根本,
便是因为她生了苏承轩这个儿子——这是永安侯目前唯一的独子,是侯府未来的继承人。
我想到小说原文里苏承轩的结局,他被复仇归来的女主精心设计,
和春风楼的花魁苟且在一起,不仅染上了难以启齿的脏病,还被引诱着染上了赌瘾,
输光了侯府不少家产,最终身败名裂,成了柳姨娘的拖累,
也成了女主复仇计划里的一枚棋子。而现在,苏承轩还没被女主设计,
依旧是那个被柳姨娘宠得无法无天、眼高于顶,却又单纯易骗的侯府公子。
一个大胆的念头在我心里渐渐成型:我不如先主动靠近苏承轩,借着他的势力,
摆脱洗脚婢的身份,一步步提升自己的地位,护住小翠。等日后女主从庄子上回来,
我再寻机会与她达成同盟——我知晓她的复仇计划,知晓柳姨娘和苏承轩的软肋,
而她需要人手,需要一个能在侯府内部为她传递消息、暗中相助的人。我们各取所需,
她报她的杀母之仇,我求我的安稳,这便是眼下最好的出路。念头既定,
我便开始不动声色地布局,不敢有半分急躁——洗脚婢与侯府公子,云泥之别,
太过刻意只会引火烧身,甚至连累小翠。我先从最基础的小事做起,借着搓洗靴子的便利,
悄悄留意苏承轩的行踪。小说里提过,他性子娇纵,最不耐等候,
却极爱后院那棵老海棠下的凉椅,每日午后都会带着小厮去那里歇脚,喝一杯冰镇的酸梅汤,
或是把玩新买的玩意儿。我特意求了负责分发杂活的管事嬷嬷,借着“柴房离海棠院近,
方便送热水”的由头,揽下了每日午后给海棠院送热水的活计。第一次去时,
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,低着头,额前的碎发遮住眉眼,双手稳稳端着铜盆,脚步放得极轻,
生怕惊扰了那位贵人,也怕被柳姨娘的眼线看出破绽。远远地,
我就看见苏承轩斜倚在凉椅上,一身月白色锦袍,手摇折扇,眉眼间满是被宠坏的慵懒,
身边的小厮正小心翼翼地替他剥着果子。我屏住呼吸,快步走到廊下,屈膝行礼,
声音压得又轻又柔,带着恰到好处的卑微:“公子,热水来了。”苏承轩果然没正眼瞧我,
只随意挥了挥手,语气不耐烦:“放那儿吧,别碍眼。”我依言放下铜盆,
指尖不经意间碰到盆沿,烫得微微发麻,却依旧低着头,不敢多停留,转身时脚步极轻,
只留下一抹匆匆的背影。我知道,第一次见面,无需让他记住我,只要不引起他的反感,
便是成功。往后几日,我每日准时送热水,依旧低眉顺眼,沉默寡言,
只在他吩咐时才敢应声,语气始终恭敬谦卑。偶尔,
他会因小厮剥的果子不够甜、酸梅汤不够冰而发脾气,摔碎茶杯,呵斥下人,
我便趁着收拾残局的间隙,悄悄留下,动作麻利地清理干净,
连地上的碎瓷片都捡得一丝不剩,从不抱怨半句。有一次,
他随手将沾了墨渍的锦帕扔在地上,身边的小厮们都怕挨骂,不敢上前,我恰好送完热水,
见状便默默走过去,捡起锦帕,轻声道:“公子,奴婢帮您拿去清洗干净,明日便好。
”这一次,苏承轩终于抬眼多看了我一眼。他的目光扫过我的粗布衣裳,
又落在我布满茧子却干净利落的手上,眉头微蹙,语气依旧带着娇纵,
却少了几分刻意的呵斥:“你是谁家的婢子?倒是比这些废物利落些。”我的心猛地一跳,
知道机会来了,却依旧不敢抬头,恭声道:“回公子,奴婢是后院的洗脚婢,贱名不值一提,
只求能替公子分忧。”说完,便捧着锦帕,快步退了出去,不敢有半分停留,生怕言多必失。
我连夜将那方锦帕清洗干净,用皂角反复搓揉,又借着月光晒干,仔细抚平褶皱,
第二天送热水时,小心翼翼地递还给她。苏承轩接过锦帕,见上面的墨渍清洗得一丝不剩,
锦帕依旧柔软顺滑,眼底闪过一丝诧异,随口道:“倒是能干。以后,你便不用送热水了,
每日来海棠院伺候,替我收拾屋子、清洗衣物便好。”听到这句话,我强压下心底的狂喜,
屈膝跪地,恭敬地磕了个头:“谢公子恩典,奴婢定当尽心伺候,不敢有半分懈怠。
”起身时,我眼角的余光瞥见小翠站在不远处的拐角,眼神里满是担忧,
我悄悄朝她摇了摇头,示意她安心。走出海棠院,风拂过脸颊,我才感觉到掌心全是冷汗。
这只是第一步,我成功摆脱了洗脚婢的身份,离苏承轩近了一步,
也离护住小翠、往上爬的目标,近了一步。可我也清楚,柳姨娘的眼线遍布侯府,
苏承轩的娇纵易骗背后,藏着无数危机。我必须步步为营,小心翼翼,既要讨好苏承轩,
借着他的势力站稳脚跟,又要隐藏自己的心思,避开柳姨娘的猜忌,
静静等待女主归来的那一天。皂角的涩味似乎还萦绕在鼻尖,只是这一次,那味道里,
不再只有绝望,更藏着一丝隐忍的希望,和步步为营的算计。我以为自己做得足够隐蔽,
却忘了柳姨娘何等精明狠辣。她能稳居妾位,凭一己之力谋害正妻、陷害嫡女,
靠的从来不是永安侯的宠爱,而是滴水不漏的心思和遍布侯府的眼线。不过半月有余,
便有人将我伺候苏承轩的模样,一字不落地上报给了她。那日我刚收拾完苏承轩的书房,
正准备去柴房给小翠送几块我攒下的点心,刚走出海棠院的拐角,
就被两个身材高大的婆子拦住了去路。她们面色冰冷,眼神锐利,不由分说地架起我的胳膊,
语气刻薄:“贱婢,姨娘有请,识相点就别挣扎,免得吃苦头!”我的心猛地一沉,
指尖瞬间冰凉——我知道,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。我挣扎着想要挣脱,却被婆子们死死按住,
力道大得几乎要捏碎我的骨头,只能被硬生生拖拽着,往柳姨娘的汀兰院走去。
汀兰院布置得奢华精致,处处透着柳姨娘的张扬,可院子里的气氛,却冷得让人窒息。
柳姨娘斜倚在铺着狐裘的软榻上,一身石榴红锦袍,妆容精致,眉眼间却没有半分暖意,
那双丹凤眼扫过来时,像淬了毒的刀子,直直扎在我身上,让我浑身发冷。我慌忙屈膝跪地,
头埋得极低,声音恭敬却克制:“奴婢参见姨娘。”柳姨娘没有让我起身,只端着茶盏,
慢悠悠地啜了一口,语气慵懒却带着刺骨的寒意:“抬起头来。”我咬了咬唇,缓缓抬头,
不敢与她对视,只垂着眼帘,假装怯懦。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番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