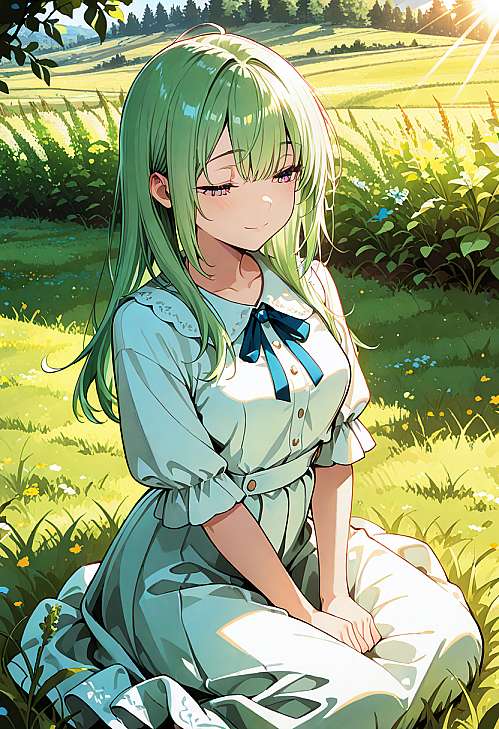导语:父亲是御前免跪的当朝太傅,我是他最宠爱的嫡女。一桩青梅竹马的婚事,
却因未婚夫的心上人砸了我家的百年招牌而掀起惊天波澜。他们以为我只是个深闺弱质,
却不知,这京城的风云,才刚刚开始。第一章“小姐,不好了!”小厮连滚带爬地冲进暖阁,
声音抖得不成调,“意欢楼……意欢楼被人给砸了!”我正临摹着母亲留下的香谱,
指尖的狼毫微微一顿,一滴墨晕在了宣纸上,像一瓣凋零的黑梅。暖阁里熏着安神的百合香,
是我亲手调配的,可此刻,那香气却压不住我心底翻涌的寒意。“说清楚。”我放下笔,
声音平稳,听不出一丝波澜。“是……是柳家那位柳如眉姑娘!”小厮跪在地上,
头都不敢抬,“她带着一群人,二话不说就开砸,还……还说……”“说什么?
”“说您要是不亲自过去给她个说法,她今天就把意欢楼的招牌给劈了,
让咱们家在京城再也做不成生意!”柳如眉。我那素未谋面的夫君,
平南侯世子萧瑾瑜的心上人。我的父亲是当朝太傅顾渊,位高权重,甚至能在御前免跪。
我是他唯一的嫡女,顾晚儿,自小便是这京城里人人艳羡的存在。
平南侯与我父是过命的交情,他老来得子,与我父亲一合计,便给我和萧瑾瑜定下了娃娃亲。
这门亲事,多年来安安稳稳,是京城的一段佳话。直到半年前,
萧瑾瑜在一次诗会上结识了吏部侍郎家的庶女,柳如眉。才子佳人,一见倾心,
很快便传得满城风雨,将我这个正牌未婚妻衬成了一个笑话。我没有哭闹,
甚至在父亲问起时,也只说相信侯府的家教。父亲心疼我,只道是我性子太过隐忍。
可他们不知道,意欢楼,是我母亲留给我唯一的嫁妆,更是我顾家的产业。自我十三岁起,
这楼里的一花一木,一账一册,都由我亲自打理。它是我在这深宅大院里,
唯一能呼吸的地方,是我用母亲所传调香之术守护的珍宝。“小姐,咱们怎么办?
柳姑娘她……她还说,是萧世子默许的。”小厮的声音里带着哭腔。我垂下眼帘,
看着自己纤细的手指。这双手,能调出世间奇香,也能拨动万贯账目。我缓缓起身,
走到窗边,看着院中那棵洗得发白的石榴树。“小姐,要不……去禀告太傅大人吧?
”“不必。”我淡淡地开口,“父亲在朝堂之上,为的是家国天下,这点后宅的腌臢事,
不必去烦他。”我的贴身侍女青黛端来一杯温茶,担忧地看着我。她跟了我多年,
知道意欢楼对我的意义。我接过茶杯,指尖触到温热的瓷壁,心中的寒意稍稍退去。“青黛,
”我轻声吩咐,“派人去楼里,告诉掌柜的,任她砸,别拦着,也别伤了自己人。但是,
给我把所有被砸坏的东西,一件一件,清清楚楚地登记在册,连块木屑都不能漏了。
”“小姐?”青黛和小厮都愣住了。“还有,”我顿了顿,眼中闪过一丝无人察觉的锐利,
“去查一查,柳如眉砸坏的那几架紫檀木博古架,是哪家木行出的货,最近的市价几何。
”小厮一怔,下意识回答:“回小姐,那是‘御木轩’的货,老师傅亲手雕的,
一套就值上千两银子,柳姑娘她们……她们全给砸了。”“很好。”我点了点头,
脸上依旧平静。无人看见,我藏在宽大袖袍下的手,早已攥得指节发白。指甲深深嵌入掌心,
传来一阵刺痛。柳如眉,萧瑾瑜。你们以为我顾晚儿是个任人拿捏的软柿子。
那就让你们看看,这柿子,到底有多硬。夜幕降临,柳如眉带着人扬长而去,
意欢楼一片狼藉。她放出狠话,说明日午时,若我再不出现,她就要当着全京城人的面,
亲手摘了“意欢楼”的牌匾。我独自坐在灯下,手里摩挲着一枚不起眼的沉香木佩,
这是母亲留给我的,也是意欢楼真正主人的信物。灯火摇曳,将我的影子拉得忽明忽暗。
压抑了许久的怒火,在心底无声地燃烧。第二章第二日,天刚蒙蒙亮,
意欢楼的掌柜就匆匆递来了消息。柳如眉变本加厉,竟派了些地痞流氓守在楼外,
但凡有老主顾上门,便上前寻衅滋-事,言语污秽不堪,吓跑了不少客人。意欢楼的声誉,
正在被一点点地摧毁。“小姐,那些人还……还对咱们的伙计动手动脚,王伯去理论,
被推倒在地,胳膊都划伤了。”青黛红着眼眶,声音哽咽。王伯是楼里的老人,
自我母亲在时便在了,待我如亲生女儿一般。我胸口一阵窒闷,
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。母亲的笑颜,王伯慈祥的脸庞,伙计们勤恳的身影,
一一在我眼前闪过。意欢楼不仅是我的心血,更是这些人的安身立命之所。“萧瑾瑜呢?
”我问道,声音里带着一丝自己都未曾察觉的颤抖。“世子他……他昨日也在场,
就站在柳姑娘身边,一言不发。”好,好一个一言不发。我深吸一口气,压下心头的翻腾。
我不能倒下,更不能冲动。父亲在朝中树大招风,我若此时闹大,
只会给政敌递上攻讦他的把柄。为了顾全大局,为了守护母亲留下的这点念想,我必须忍。
“小姐,要不……我们去求求柳姑娘吧?”青黛小心翼翼地提议,“她是吏部侍郎的女儿,
咱们备些厚礼,说几句软话,兴许她就高抬贵手了。”求她?我心中一阵苦涩。我顾晚儿,
堂堂太傅嫡女,竟要向一个庶女低头求饶。可看着青黛担忧的脸,想到王伯的伤,
我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我写了一封信,言辞恳切,只说意欢楼乃先母遗物,若有得罪之处,
我愿备薄礼登门致歉,请她高抬贵手,放过楼里的伙计。我让掌柜的亲自送去,
并带上了库房里最名贵的一支南海珍珠钗。然而,我等来的,是更大的羞辱。掌柜回来时,
衣衫不整,脸上还有一个清晰的巴掌印。他跪在地上,老泪纵横。“小姐,
老奴没用……那柳姑娘,她……她当着所有人的面,把您的信撕了,把珠钗扔在地上,
还……还说……”“说什么?”我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。“说太傅府的嫡女,
就是个只会躲在龟壳里的缩头乌D,连自己的产业都护不住,不配做萧世子的正妻!
她让老奴滚回来告诉您,午时之前,您若不亲自去意欢楼门前,跪下给她奉茶认错,
她就要当众烧了那块牌匾!”“砰!”我手中的茶杯,应声落地,摔得粉碎。
茶水溅湿了我的裙摆,滚烫的温度仿佛灼烧着我的皮肤。跪下奉茶?烧了牌匾?
她这是要将我,将整个太傅府的脸面,都踩在脚底下!那一刻,我脑海里一片空白。
我甚至想过,干脆关了意欢楼,从此不问世事。可母亲临终前拉着我的手,
让我定要好好守护它的样子,又浮现在眼前。“小姐……”青黛吓得脸色发白。我闭上眼,
再睁开时,眼中已是一片决然。“青黛,去账房,取五百两银票。”我冷静地吩咐道。
“小姐,您这是……”“王伯的伤,还有其他伙计的惊吓,都要安抚。另外,
去‘济世堂’请最好的大夫,买最好的伤药。”我条理清晰地安排着,“告诉所有人,
今日楼里歇业一天,工钱照发,让他们安心养伤。”安排好一切,我独自回到书房。
打开一个暗格,里面放着一个小小的紫檀木盒。盒子里,不是金银珠宝,
而是一叠陈旧的信笺和一块玄铁令牌。这是我母亲留下的,属于意欢楼真正的底牌。多年来,
我一直遵守着母亲的遗愿,只把意欢楼当做一个普通的香料铺子经营,从未动用过这些力量。
但现在,他们欺人太甚。午时将至,京城最繁华的朱雀大街上,意欢楼门前已是人山人海。
柳如眉一身华服,得意洋洋地站在中央,她身边,站着身姿挺拔、面容冷峻的萧瑾瑜。
他们身后,几个家丁已经架好了火把。“时辰快到了,看来顾大小姐是不会来了。
”柳如眉娇笑着,声音不大,却足以让周围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,“既然如此,
也别怪我……”她话音未落,人群忽然一阵骚动。一顶素雅的青呢小轿,
在太傅府侍卫的护送下,缓缓停在了意欢楼门前。我,顾晚儿,来了。第三章轿帘掀开,
我扶着青黛的手,缓步而出。今日,我未着华服,仅一身月白素裙,
裙角绣着几支清雅的兰草。发髻上除了一根白玉簪,再无别物。面容平静,眼神淡漠,
仿佛眼前这场闹剧,与我毫无干系。所有人的目光,瞬间聚焦在我身上。有惊讶,有同情,
有幸灾乐祸。柳如眉显然没料到我真的敢来,先是一愣,随即脸上露出胜利者的笑容。
她上下打量着我,语气中满是轻蔑:“哟,我当是谁呢,原来是顾大小姐。怎么,
终于肯从你的龟壳里出来了?”萧瑾瑜的目光也落在我身上,复杂难辨。他眉头微蹙,
似乎想说什么,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。我没有理会柳如眉的挑衅,
只是静静地看着那块悬挂在门楣上,历经风雨的牌匾。
那是前朝大儒亲笔题写的“意欢楼”三个字,笔锋苍劲,古朴大气。“柳姑娘,
”我终于开口,声音不大,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,“你说,要我给你一个说法?
”“没错!”柳如眉扬起下巴,“你霸占着世子未婚妻的名分,不知廉耻。今天,
你要么当众宣布与世子解除婚约,要么,就跪下给我奉茶认错!
”人群中发出一阵倒吸冷气的声音。当众退婚,对女子而言,是奇耻大辱。跪下奉茶,
更是将太傅府的尊严踩在脚下。我笑了,极轻极淡地笑了一下。“婚约,是父母之命,
媒 灼之言,由不得你我。至于奉茶认错……”我顿了顿,目光如冰刃般扫过她,
“我顾晚儿,上跪天地君亲师,你,算什么东西?”“你!”柳如眉的脸瞬间涨得通红。
“我算什么东西?”她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,指着身旁的萧瑾瑜,“我是世子心尖上的人!
而你,不过是个没人要的弃妇!”“啪!”一声清脆的耳光,响彻全场。所有人都惊呆了。
我收回手,依旧站在原地,仿佛刚才动手的不是我。柳如眉捂着脸,难以置信地看着我,
眼中瞬间涌上泪水:“你……你敢打我?”“这一巴掌,是替我母亲打的。
”我的声音冷得像冰,“意欢楼是她的心血,你在此撒野,便是对她的不敬。”“来人!
给我上!把这贱人的手给我废了!”柳如眉尖叫起来。
她身后的几个家丁立刻凶神恶煞地围了上来。然而,他们还没靠近我,
就被我带来的侍卫拦住了。这些侍卫都是父亲从军中挑选的精锐,以一当十,
岂是这些乌合之众能比的。“顾晚儿!”萧瑾瑜终于开口,语气中带着怒意,
“你闹够了没有!?”我转向他,这是半年来,我第一次正眼看他。“萧世子,这句话,
该我问你。”我看着他,一字一句道,“你纵容你的心上人,打砸我的店铺,欺辱我的伙计,
羞辱我的名声。如今,你倒问我闹够了没有?”“我……”萧瑾瑜一时语塞。“萧瑾瑜,
我只问你一句。”我逼视着他的眼睛,“昨日,柳如眉砸我意欢楼,你可知情?
”他眼神闪躲,没有回答。“今日,她逼我下跪,你可赞同?”他依旧沉默。
我心中最后一点念想,彻底熄灭。“好。”我点了点头,不再看他。我转向人群,
朗声道:“各位乡亲父老,今日之事,是非曲直,想必各位心中自有公断。
”我从青黛手中拿过一本册子,高高举起。“这是昨日柳姑娘在我意-欢楼中,
砸坏的所有物品清单。其中,御木轩的紫檀博古架两座,
市价三千二百两;前朝官窑青花瓷瓶一对,市价八百两;西域进贡的琉璃灯盏一盏,
市价五百两……”我每念出一件,柳如眉的脸色就白一分。周围的人群更是议论纷纷。
“……零零总总,共计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两白银。”我合上册子,目光锁定柳如眉,
“柳姑娘,吏部侍郎一年的俸禄,也不过三百两。不知这笔钱,你是打算自己赔,
还是让吏部侍郎大人,或是平南侯府,替你赔?”柳如眉彻底慌了,她求助地看向萧瑾瑜。
萧瑾瑜的脸色也极为难看。一万多两,对他而言也不是小数目,更重要的是,
此事一旦闹上公堂,丢的是整个平南侯府的脸。“晚儿,得饶人处且饶人。”他终于服软。
“饶人?”我冷笑,“我的人被-打伤时,你们可曾想过饶人?我的百年招牌险些被毁时,
你们可曾想过饶人?”我的声音陡然拔高,带着前所未有的强硬:“今日,要么,赔钱道歉,
从此不得踏入意欢楼半步。要么,我们公堂上见!”柳如眉吓得浑身发抖,萧瑾瑜脸色铁青。
最终,在众目睽睽之下,萧瑾瑜咬着牙,写下了一张一万四千两的银票,塞到我手里。
柳如眉则在我的逼视下,不情不愿地道了歉。我接过银票,看也未看,直接交给了掌柜。
“多出来的,给受伤的伙计们分了,压压惊。”然后,我转身,
对依旧呆立的萧瑾瑜和柳如眉说:“再敢动我的人,动我的东西,我顾晚儿,绝不客气。
”说完,我不再停留,转身登轿离去。轿子起行的瞬间,我攥紧的拳头才缓缓松开,
掌心一片湿冷。眼底的决绝和释然交织,我知道,从今天起,一切都不同了。
第四章我当街掌掴柳如眉,逼得平南侯世子赔偿万两白银的消息,像长了翅膀一样,
一夜之间传遍了京城。坊间的风向,一夜之间全变了。从前人们说起我,
是“温婉贤淑”、“可惜被辜负”的同情。现在,
则变成了“深藏不露”、“不愧是顾太傅的女儿”的敬畏。那些曾经对我指指点点的邻里,
如今见了太傅府的马车,都远远地驻足行礼。意欢楼的生意,不仅没有受损,反而因祸得福,
宾客络绎不绝,都想来见识一下这位传奇女主人的风采。最让我欣慰的,是父亲的态度。
他听闻了整件事的始末,非但没有责备我行事张扬,反而在书房里,对着母亲的画像,
轻声说了一句:“阿秀,我们的女儿长大了,像你。”然而,风平浪静之下,
是更汹涌的暗流。柳如眉和萧瑾瑜吃了这么大的亏,自然不会善罢甘休。
他们的报复来得很快。柳如眉不知从哪儿请来一位据说是宫里出来的调香圣手,
在京城另一头开了家“闻香榭”,处处模仿意欢楼的陈设,价格却低了三成,还放出话去,
说意欢楼的香方都是陈旧过时的。同时,平南侯府那边,侯夫人亲自出面,
开始在各家贵妇的宴会上,或明或暗地散播我的谣言,说我善妒、跋扈,毫无容人之量,
将来必不是贤妻。想以此败坏我的名声,逼我主动退婚。一时间,我再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。
青黛急得团团转:“小姐,这可怎么办?闻香榭抢了我们好多生意,
那些夫人们也开始对您有微词了。”我却只是笑了笑,不慌不忙地取出一张新的香谱。
“慌什么。”我一边研墨,一边道,“跳梁小丑,让他多蹦跶几天。正好,
也让京城的人看看,什么是真正的东施效颦。”三日后,意欢楼宣布,
将推出一款举世无双的新香,名为“刹那芳华”。为了一睹为快,
京中名流贵妇几乎悉数到场,就连深居简出的长公主殿下,也派人送来了贺礼。
我换上一身海棠红的衣裙,亲自登台。当着所有人的面,我没有多言,
只是将那“刹那芳华”的香膏,轻轻点燃。一股奇异的香气,瞬间弥漫了整个大堂。
初闻是清冽的梅香,仿佛置身于寒冬的雪地;细品之下,又有暖阳般的牡丹香气涌现,
带来春日的暖意;尾调则变为沉静的檀香,悠远绵长,令人心安。一款香,
竟能品出四季更迭,人生百味。全场寂静,所有人都沉醉其中。这时,
我才缓缓开口:“此香,看似一体,实则由十二种不同香料,以特殊手法分层融合而成。
点燃后,随温度变化,香气亦随之流转,故名‘刹那芳华’。”我话音刚落,
台下已是一片惊叹。“顾小姐真是神乎其技!”“这等奇香,闻所未闻!”而就在此时,
闻香榭的掌柜带着那位“调香圣手”不请自来,手中还捧着他们的新品,
意图当场与我一较高下。我看着那位所谓的“圣手”,微微一笑:“阁下既是宫中出来的,
想必认得此物。”我让青黛呈上一枚小巧的银质香囊,上面绣着一个独特的徽记。
那“圣手”一见,脸色大变,当场跪了下来:“小人……小人有眼不识泰山,
不知是‘南香苑’的主人当面!”“南香苑”,是我母亲的师门,执掌天下调香之术牛耳,
其门人遍布天下,甚至宫中御用的调香师,都出自其门下。而我手中的香囊,
正是“南香苑”少主的信物。真相大白。那所谓的“圣手”,
不过是“南香苑”一个被逐出师门的外门弟子,学了点皮毛,就敢出来招摇撞骗。
他调制的香,连“刹那芳华”的万分之一都不及。闻香榭,彻底成了一个笑话。
解决了生意上的麻烦,我转而对付侯府的谣言。我没有去与那些长舌妇争辩,
而是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。我以太傅府的名义,在城外开设粥棚,救济流民。
同时,将意欢楼当月盈利的一半,捐给了京中的慈幼局。一时间,
顾家大小姐“心善仁厚”之名,传遍大街小巷。那些关于我“善妒跋扈”的谣言,不攻自破。
做完这一切,我写了一封信,派人送往平南侯府。信中,我并未提及退婚,
也未指责侯夫人的所作所为。我只是以晚辈的口吻,
详细阐述了开设粥棚和捐助慈幼局的初衷,并恳请侯府作为姻亲,
也能为京中百姓尽一份心力,共积福报。这封信,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,
打在了平南侯的脸上。他把我捧到了道德的高点,自己若是不做,
便坐实了刻薄之名;若是跟着做,就等于是向我低头认输。当晚,平南侯亲自登门,
向我父亲致歉,并送来了厚重的赔礼。据说,萧瑾瑜被他用家法打得三天没下得了床,
侯夫人也被禁足佛堂,静心思过。我站在窗前,看着侯府的马车在夜色中远去,
心中没有半分喜悦,反而愈发凝重。柳如眉和萧瑾瑜,不过是被人推到台前的棋子。
他们的手段,看似狠辣,实则幼稚。而真正想对付顾家的人,还藏在更深的暗处。我的反击,
只是刚刚开始。第五章风波暂时平息,意欢楼的生意蒸蒸日上。但我心里清楚,
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我让掌柜暗中调查闻香榭的资金来源。很快,
线索就指向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——靖王府。靖王,当今圣上的亲弟弟,素有贤名,
却在朝中一直与我父亲政见不合。表面上,他与世无争,可我知道,越是平静的湖面下,
越可能藏着噬人的巨兽。一个亲王,为何要费尽心机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