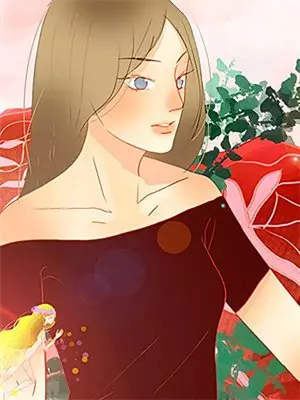
雾锁月牙湾浓得化不开的海雾,裹挟着鲛人族特有的海草腥气,像一床厚重的湿棉被,
将月牙湾捂得严严实实。雾是凌晨时分悄然登陆的,不过两个时辰,
整个渔村便成了白茫茫的孤岛,连村口那株百年老榕树的轮廓都模糊了,
只剩下一团深色的影子。阿水站在榕树下,手搭凉棚望向波涛汹涌的海面。
雾让视线变得毫无意义,但他依然保持着这个姿势——这是渔家人的习惯,
眼睛看不见的时候,就用耳朵听,用鼻子闻,用皮肤感受风的走向。“第三次了。
”他低声自语,声音被雾气吸收得一干二净。这个月,
海雾已经第三次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席卷月牙湾。更诡异的是,每一次大雾降临,
都伴随着鲛人袭击的传言。村东的渔场被毁,晾晒的渔网被撕成碎片,
渔船的船舷上留下深深的抓痕——那痕迹绝非普通海洋生物所能留下。“来了!又来了!
”村西头的铁蛋从雾中冲出来,像一头受惊的小鹿。他今年十七岁,比阿水小三岁,
是村里最机灵也最胆小的年轻人。此刻他脸色惨白,手里的渔网还没放下,
网眼上挂着几片银蓝色的东西,在昏黄的晨光中泛着诡异的光泽。
“东边的渔场...全毁了!”铁蛋的声音带着哭腔,“李老头的船被掀翻,人掉进海里,
要不是柱子眼疾手快...”“人怎么样?”阿水立刻问,接过他手里的渔网。
“呛了几口水,吓得不轻,送回家歇着了。”铁蛋喘着气,压低声音,
“还有...他们又留下了这个。”他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,小心翼翼地递给阿水。
那是一枚鳞片。巴掌大小,银蓝色,边缘锋利如刀。阿水接过鳞片时,指尖传来刺骨的寒意,
那寒意顺着手指迅速蔓延,几乎让他打了个寒颤。
他将鳞片举到眼前细看——鳞片表面有着极其精细的纹路,像是某种古老的文字,
又像是海浪的图案。光线在纹路间流动,仿佛鳞片本身是活的。“给我看看。
”苍老却威严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村长陈海拄着雕花檀木拐杖缓步走来,
位有头有脸的人物——账房先生老周、船老大赵广、还有最近刚在村里开起杂货铺的郑掌柜。
他们像是早就约好了似的,在雾气最浓的时刻集体出现。陈海今年六十二岁,
担任月牙湾村长已经二十年。他身材不高,背有些微驼,但眼神锐利如鹰。
年轻时他是这一带最好的渔把头,能在风暴来临前三个时辰就闻到危险的气息。
如今年纪大了,那份敏锐似乎转化成了另一种东西——一种深不可测的城府。
阿水将鳞片递过去。陈海接过的动作很慢,很稳,但阿水敏锐地捕捉到,
在指尖触到鳞片的那一刹那,村长的手几不可察地颤抖了一下。那不是恐惧,
更像是一种...确认。“是鲛人鳞片无疑。”陈海叹了口气,
皱纹密布的脸上露出悲悯的神色,“祖先们常说,鲛人记仇,千年不忘。看来,
我们月牙湾这次是惹上大麻烦了。”人群中响起窃窃私语。恐惧像瘟疫般在浓雾中蔓延。
阿水注意到,
许多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村中央那座新建成的祠堂——那是三个月前开始动工的,
用的是来自深海的上等红珊瑚和珍珠母贝装饰,奢华得与这个偏僻渔村格格不入。
祠堂的屋檐上,还挂着几串风干的奇异海草,据说是从数百里外的外海打捞上来的。
“大家不要慌。”陈海举起手,声音沉稳有力,“我已经派人去请青云观的道长了。
青玄道长法力高深,定能驱除妖邪,保我月牙湾平安。”账房老周立刻附和:“村长说得对,
有青玄道长在,什么鲛人海怪都不足为惧。”“在此之前,”陈海继续说道,目光扫过众人,
“所有人不得私自出海,夜晚必须紧闭门户。阿水——”他的目光落在阿水身上。
“你年轻力壮,又熟悉海况,组织些年轻人夜间巡逻,保护好村子。”阿水点头应下:“是,
村长。”他心里却隐隐觉得不对劲。如果鲛人真的只是传说中的生物,为何袭击如此精准?
每次都针对渔船和渔场,却不曾伤人性命,最多只是吓唬——李老头被掀进海里,
但立刻就被救了上来;渔网被撕碎,但晾晒的鱼干却完好无损。这不像复仇,
倒像是在...警告。而且,陈海的反应也太镇定了。
一个传说中凶残无比的海妖族群正在袭击自己的村庄,作为村长,
他的担忧似乎只停留在表面。阿水想起三个月前,
陈海组织的那几次“远海捕捞”——说是为了给村里增加收入,要去外海寻找珍稀海产。
去的都是他的亲信,回来后闭口不谈捕捞细节,但村里很快就开始了大规模建设。“阿水哥,
现在怎么办?”铁蛋小声问,把阿水从思绪中拉回来。“先组织人巡逻。”阿水说,
“你去叫柱子、大牛、水生他们,晚饭后在榕树下集合。”铁蛋点点头,转身跑进雾中。
阿水看着他的背影消失,又看了看手中的鲛人鳞片。寒意还在指尖徘徊,但奇怪的是,
那股寒意并不让他感到不适,反而有种莫名的熟悉感。他从小就和别的孩子不太一样。
别的孩子怕水,他却能在海里泡上一整天;别的孩子在暴风雨来临时躲在家里,
他却能站在礁石上,感受海浪每一次拍击的力度和节奏;最奇怪的是,
他能在水下闭气的时间长得惊人——有一次渔船倾覆,
他在水下待了将近一炷香的时间才浮上来,把救他的人吓得半死。
爷爷在世时曾说:“阿水啊,你身上流着海的血。”那时他以为这只是渔家人的比喻。
但现在,握着这枚鲛人鳞片,那句话突然有了新的含义。夜幕降临,雾气非但没有散去,
反而更加浓重。海风裹挟着咸湿的气息吹拂着月牙湾,将雾搅动成诡异的形状。
阿水带着铁蛋、柱子等八个年轻人在村边巡逻。每人手里都拿着鱼叉或船桨,
腰间别着防身的匕首。月光被浓雾过滤得只剩下一团惨白的光晕,远处的海面漆黑如墨,
只有波涛拍岸的声音单调地重复着,像巨兽的呼吸。“阿水哥,你说鲛人长什么样?
”铁蛋压低声音问道,手里的鱼叉握得太紧,指节都发白了。“我爷爷说过,
他们上半身像人,下半身是鱼尾,住在深海的水晶宫里。”柱子接话道,
“还说他们的歌声能迷惑人心,听见的人会不由自主地跳进海里。”“那都是传说。
”阿水说,眼睛警惕地扫视着浓雾笼罩的海岸线,“真要有那种歌声,咱们月牙湾早没人了。
”“可是袭击是真的啊。”大牛粗声粗气地说,“我今早去看了,渔场的栅栏被整个掀翻了,
那力气,不是人力能做到的。”阿水没有回答。这个问题也在他心中盘旋。
月牙湾世代以捕鱼为生,虽然偶有捕获珍稀海产的情况——比如罕见的金枪鱼、玳瑁,
甚至有一次还捞上来一具鲸骨——但村民们大多朴实本分,从未听说过与鲛人结怨的传说。
如果鲛人真的存在,他们为什么要攻击月牙湾?“嘘——”阿水突然抬手,
所有人都屏住呼吸。雾中传来了声音。不是海浪声,也不是风声,
而是一种若有若无的...歌声。起初极其微弱,像远处飘来的呓语,但渐渐清晰起来。
那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声音,空灵、哀婉,如泣如诉,穿透浓雾直抵人心。柱子第一个中招。
他的眼神突然变得空洞,鱼叉从手中滑落,哐当一声掉在地上。但他毫无知觉,
只是直勾勾地望着海的方向,迈开脚步朝海边走去。接着是铁蛋、大牛...除了阿水,
所有年轻人都像被无形的线牵引着,神情恍惚地走向大海。“醒醒!
”阿水用力推了柱子一把,同时咬破舌尖。剧痛让他保持清醒,
但歌声的魔力依然在拉扯他的意识。奇怪的是,
那歌声对他似乎有种天然的抵抗力——不是完全无效,但至少他能保持基本的判断力。
他拽住柱子的胳膊,又去拉铁蛋,但两个人像中了邪似的力大无穷。情急之下,
阿水从腰间解下装淡水的皮囊,拧开盖子,将水泼在几人脸上。
冰冷的海水让铁蛋打了个激灵,
眼神恢复了一丝清明:“阿水哥...我...”“待在这里!捂住耳朵!”阿水吼道,
将皮囊塞给铁蛋,“用水泼醒他们!”说罢,他独自循着歌声的方向走去。
那歌声来自海湾最隐蔽的一处礁石区,那里暗礁密布,平时连渔船都不会靠近。
阿水小心翼翼地踩着湿滑的礁石,浓雾让能见度不足五米,
他只能凭着对地形的熟悉和歌声的指引前进。然后,他看到了。月光透过雾的缝隙,
斑驳地洒在海面上。三个身影半浮于水中,倚在一块巨大的黑色礁石旁。
她们有着人类的面容,却美丽得不似凡人——皮肤苍白如珍珠,眼睛是深邃的海蓝色,
银蓝色的长发如海藻般在水中飘荡。而下半身,是覆盖着细密鳞片的鱼尾,
那鳞片正是阿水白天见到的那种银蓝色,在水中轻轻摆动时,折射出梦幻般的光泽。鲛人。
传说中的生物真的存在。其中一个看起来最年轻的鲛人正唱着歌,她的眼中含着泪,
泪珠滚落时,竟在空气中凝结成莹白的珍珠,扑通扑通沉入海底。她的歌声哀伤至极,
每一个音符都浸透着绝望。年长的鲛人突然抬手,示意停止歌唱。她转过头,
三双眼睛同时聚焦在阿水身上。阿水本能地后退一步,脚下一滑,差点跌进海里。
但他稳住身形,手已经摸到了腰间的匕首。然而鲛人们没有攻击的意思。
年长的鲛人游近一些,她的鱼尾在海水中划出优雅的弧线。月光照在她脸上,阿水这才看清,
她的眼角有细细的皱纹,像是经历过漫长岁月。她用生涩的人类语言说道:“你...不同。
你身上...有海的味道。”阿水一愣:“我是渔村的孩子,自然有海的味道。”鲛人摇头,
指了指自己的心口:“这里...海的回声。你...不全是人类。
”这句话如惊雷般在阿水心中炸开。他想起爷爷的话,想起自己所有异于常人的地方。
但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,现在不是探究身世的时候。“你们为什么要袭击我们的村子?
”阿水直截了当地问。年长鲛人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,
像是淬了寒冰的海水:“带走...我们的族人。囚禁...折磨。换你们...财富。
”她指着村中灯火辉煌的方向——那是村长家新建的别院,“那里...有我们族人的痛苦。
”阿水的心沉了下去。他顺着鲛人手指的方向望去,村长的别院在夜色中格外醒目,
窗户里透出温暖的黄光,隐约能看到里面摆放着各种珍奇摆件。
“你们怎么确定是我们抓了你们的族人?”年幼的鲛人突然激动起来,
一串珍珠般的眼泪滚落:“姐姐!他们带走了姐姐!
我看见了...人类的大船...网...”她的语言支离破碎,但阿水听懂了关键信息。
三个鲛人中,中间的那个一直沉默着,此时突然开口,
声音沙哑:“三个月前...月圆之夜。大船...铁网。
姐姐被拖走...血...海里有血。”“三个月前,月圆之夜。”阿水重复道,
心中那个怀疑的种子开始疯长。三个月前的月圆之夜,
正是陈海组织“远海捕捞”的日子之一。那天去了三艘大船,回来后,陈海宣布收获颇丰,
但具体是什么收获,却讳莫如深。“我会调查清楚。”阿水郑重承诺,
“如果真是我们的人抓了你们的族人,我会尽力救她出来。”年长鲛人深深看了他一眼,
那眼神复杂难明——有怀疑,有期待,还有深藏的悲哀:“你...七天。
不然...海将吞噬一切。”“七天之内,我会给你们一个交代。”阿水说。鲛人点点头,
对同伴说了几句阿水听不懂的语言,声音如流水潺潺。然后,三人缓缓潜入水中,
消失得无影无踪,只余下海面荡漾的涟漪,和几颗沉在礁石缝里的珍珠。阿水弯腰捡起一颗。
珍珠在他掌心泛着温润的光泽,触手微凉。他将珍珠收好,转身返回。
铁蛋他们已经完全清醒了,正惶恐不安地聚在一起。看到阿水回来,都围了上来。“阿水哥,
那歌声...”“是鲛人。”阿水平静地说,看到众人惊骇的表情,补充道,
“但我跟她们谈过了。”他将所见所闻简单说了一遍,隐去了关于自己身世的猜测。
几个年轻人都震惊不已。“村长他...真的会做这种事吗?”铁蛋难以置信,
“他可是村长啊。”柱子却若有所思:“三个月前那几次出海,我爹本来也要去的,
但村长说人够了。后来那些去了的人,回来都闭口不谈,但我见过赵广叔家里多了个玉镯子,
他婆娘到处显摆。”“我也有印象。”大牛说,“郑掌柜的杂货铺,就是那之后开起来的。
他以前就是个跑船的,哪来那么多本钱?”疑点越来越多。
阿水心中那个模糊的猜测逐渐清晰起来。“今晚的事,谁都不要说出去。
”阿水严肃地看着众人,“我们需要证据。明天开始,大家留意那些跟村长出过海的人,
看看他们最近有没有不寻常的举动。但记住,不要打草惊蛇。”几人点头。
他们都是阿水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,彼此信任。“阿水哥,
如果村长真的抓了鲛人...我们怎么办?”铁蛋小声问。“那就救她出来。
”阿水毫不犹豫地说,“无论对方是不是人类,囚禁和折磨都是错的。”夜色更深了。
阿水回到家——一间简陋的渔家小屋,父母早逝,只有爷爷留下的几件旧家具和一些渔具。
他躺在床上,却毫无睡意。掌心那枚鲛人珍珠微微发烫,像是在提醒他那个七天的约定。
窗外的海雾依然浓重。阿水突然想起爷爷临终前的话:“阿水,月牙湾的平衡很脆弱。
陆地和海洋,人类和其他生灵...一旦打破,灾难就会降临。”当时他不懂。现在,
他似乎开始明白了。深潜的秘密第二天清晨,雾气稍有散去,但天空依然阴沉,
铅灰色的云层低垂,仿佛随时会压下来。阿水像往常一样帮村民修补渔网,
耳朵却竖起来收集着各种信息。修补渔网的工作在村东头的晒场上进行,那里视野开阔,
能看见大半个村子和远处的海。七八个老渔民坐在小板凳上,手里穿梭引线,嘴里也不闲着。
“听说了吗?青云观的道长明天就到。”老李头说,他是村里最年长的渔民之一,
儿子就是前天落水的李老头。“早点来好啊,这天天提心吊胆的,谁受得了。”王伯叹气,
“我家那口子晚上都不敢合眼,说是听见海里有哭声。”“要我说,这事蹊跷。
”一直沉默的孙老爹突然开口。他是村里少数几个还在用传统方式捕鱼的老把式,
对海洋有着近乎虔诚的敬畏。“鲛人要真记仇,为什么早不来晚不来,偏偏这时候来?
还只毁东西不伤人?”阿水手里补着网,装作随口问道:“孙老爹,您觉得是为什么?
”孙老爹看了他一眼,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精光:“小子,
你爷爷在世时说过一句话——大海不会无缘无故发怒。要么是我们越界了,
要么是...有人替大海发怒了。”“越界?我们世世代代捕鱼,怎么就越界了?
”老李头不解。“捕鱼和掠夺是两码事。”孙老爹缓缓说,“你爷爷那会儿,渔网网眼多大?
小的不要,怀崽的放生。现在呢?恨不得把海里的东西一网打尽。
还有那些珊瑚、珍珠贝...那是海里的骨头和眼睛,能随便挖吗?
”阿水心中一动:“孙老爹,您知道村里最近谁在弄这些吗?”孙老爹沉默了片刻,
摇摇头:“老了,眼睛花了,什么都看不清咯。”但他说话时,
目光有意无意地瞟向村中央祠堂的方向。午饭后,阿水借口检查渔场受损情况,
在村里转了一圈。他特意路过那几个跟村长出过海的渔民家。赵广家院子里晾着新做的衣裳,
料子明显比普通渔家用的好;郑掌柜的杂货铺里,
了从城里运来的稀罕物——玻璃珠子、彩色的布匹、甚至还有几面铜镜;最可疑的是陈海家,
新建的别院气派非凡,阿水透过半开的院门,看到里面摆放着巨大的珊瑚盆景,
在阴沉的天色下依然泛着暗红的光泽。“阿水,在这儿看什么呢?”阿水回头,
见陈海不知何时出现在身后,脸上挂着惯常的和蔼笑容,但眼神深处却有一丝警惕。“村长。
”阿水镇定地点头,“我在想去渔场的路,雾太大了,差点走错。”“是啊,这雾邪门得很。
”陈海叹了口气,“不过明天青玄道长就来了,到时候一切都会好的。你晚上还要巡逻吧?
辛苦了。”“应该的。”陈海拍了拍他的肩膀:“好好干,等这事过了,
村里不会亏待你们这些年轻人的。”阿水点点头,告辞离开。走出几步后,他回头看了一眼,
发现陈海还站在原地望着他,脸上的笑容已经消失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沉的思索。
当天下午,阿水召集了铁蛋他们。几人找了个僻静的海湾,假装修补小船,
实则交流收集到的信息。“我打听到了。”柱子压低声音,“赵广家的玉镯子,
是他婆娘在城里当铺买的。当票我偷偷看了,当的是‘海珍一串’,时间正好是三个月前。
”“郑掌柜开铺子的钱,据说是‘海上运气好’。”大牛说,“我问他怎么个好法,
他支支吾吾说不清楚。”铁蛋最机灵,居然打探到了关键信息:“我听祠堂的看守老吴说,
村长家别院下面有个地下室,老吴有一次送东西,看见他们抬了个大箱子下去,
箱子里有水流出来,还有...还有怪声。”“怪声?”阿水追问。“像是...唱歌,
但又不像人唱的。”铁蛋说,“老吴吓得没敢多看。”阿水心中已经有了七八分把握。
他看看天色,太阳已经开始西沉,浓雾又从海面弥漫开来。“今晚,我们去村长家看看。
”“直接去?”柱子有些犹豫,“万一被抓住...”“我有办法。”阿水说,
“但需要你们配合。”他详细说了计划。几人听得紧张又兴奋,最后都点头同意。夜幕降临,
雾气比前两晚更浓。阿水带着铁蛋等人照常巡逻,但特意绕开了村长家所在的区域。
到了子时,他们按照计划行动。柱子和大牛在村东头制造动静——故意打翻木桶,大声呼喊,
装作发现异常。果然,村长家立刻有人出来查看,连看守别院的人都暂时离开了岗位。
阿水和铁蛋趁机从后院翻墙而入。村长家的别院比从外面看起来更加奢华。
院子里铺着从外地运来的青石板,角落里种着奇花异草,甚至还有一个小池塘,
里面养着几尾色彩斑斓的锦鲤。主屋灯火通明,
阿水能听见里面传来的谈话声——是陈海和几个亲信在商量明天迎接道长的事。
“道长那边都打点好了吗?”陈海的声音。“放心,五百两银子,他比我们还上心。
”是账房老周的声音。“那东西怎么样?”“还活着,但状态不太好。道长说,要取鲛人泪,
得先让她们绝望,再给一丝希望,反复折磨,泪珠才纯净。”阿水听得浑身发冷。
他示意铁蛋望风,自己撬开侧窗,轻手轻脚地翻入屋内。
房间里弥漫着海腥味和一种奇异的香气——像是檀香,但又混杂着某种海洋植物的味道。
阿水适应了一下昏暗的光线,发现这是一个类似书房的地方,墙上挂着各种海洋生物的标本,
书架上摆着一些古籍和瓶瓶罐罐。但最引人注目的是房间中央那个巨大的水晶缸。
缸有两米高,直径也有一米多,用整块水晶雕琢而成,价值连城。缸里注满了海水,
水面上漂浮着几片海草。而在水中...阿水走近,当他看清缸中之物时,
浑身的血液几乎凝固。那是一位女性鲛人。她比阿水昨晚见到的三个都要年长一些,
面容更加成熟美丽,但此刻却憔悴不堪。银蓝色的长发失去了光泽,
像枯死的水草般飘散在水中;下半身的鱼尾无力地垂着,鳞片多处脱落,
露出下面苍白的皮肤;身上有多处伤痕,有的已经结痂,有的还在渗着淡淡的蓝色液体。
最令人心碎的是她的眼睛——曾经应该如海洋般深邃美丽的眼眸,如今空洞无神,
只有深不见底的绝望。她的手腕和脚踝上套着金属镣铐,用细链连接,将她限制在水缸中央,
活动范围不足半米。鲛人察觉到有人靠近,惊恐地后退,撞在缸壁上,发出沉闷的响声。
链条哗啦作响,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刺耳。“别怕,我是来帮你的。
”阿水用尽可能温和的语气说,尽管知道对方可能听不懂。鲛人停止了挣扎,疑惑地看着他。
她的眼睛在阿水脸上停留片刻,突然闪过一丝微弱的光芒。她张开嘴,
发出一串流水般的声音,不是昨晚那种歌声,更像是某种语言。阿水听不懂,
但他能感觉到那声音中的疑问和...一丝熟悉感。他尝试着指了指自己,
又指了指窗外的大海,做了一个游泳的手势。鲛人的眼睛亮了一些,她艰难地抬起手,
指了指自己脖子上的项圈——那是一个金属项圈,连接着一条更粗的链子,固定在缸底。
阿水凑近查看。项圈设计精巧,锁眼很小,需要特殊的钥匙。
链子的一端固定在墙上的一个机关里,那机关造型奇特,像是某种海螺的形状。就在这时,
门外传来脚步声。阿水迅速躲到厚重的帘幕后面。门开了,陈海踱步进来,
身后跟着账房老周和船老大赵广。他走到水缸前,满意地打量着里面的鲛人,
像是在欣赏一件珍贵的收藏品。“明天青云观的道长就来了。
”陈海的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,“他说鲛人泪珠价值连城,
但需要特殊方法才能让她们落泪。到时候,我们就有取之不尽的财富了。
”赵广谄媚地说:“村长高明,用鲛人鳞片假装袭击,既转移了村民的注意力,
又能借此请来道长。等道长‘驱除’了鲛人,我们再悄悄捕几只,
月牙湾就再也不必过穷日子了。”阿水在帘幕后听得浑身发冷。他原以为村长只是贪婪,
没想到整个袭击事件都是他自导自演的阴谋!“那些蠢货,真以为是祖先惹下的仇怨。
”陈海冷笑道,“等道长做法的时候,我们就把这鲛人抬出去,
让所有人都看见‘妖物本体’,到时候道长再‘勉为其难’地收服她,一切顺理成章。
”老周有些担忧:“村长,阿水那小子最近好像有点多事。昨晚巡逻,
今天又在村里到处转悠...”“先不用管他。”陈海摆摆手,“那小子有点本事,
我还要用他来组织村民防御。等事情了结...”他没有说下去,
但语气中的寒意让帘幕后的阿水打了个寒颤。“这道长可靠吗?”赵广问。
“青玄道长在沿海一带很有名,专门处理类类‘灵异事件’。”陈海说,“只要钱给够,
他自然知道该怎么说、怎么做。等拿到第一批鲛人泪,我们就去省城,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