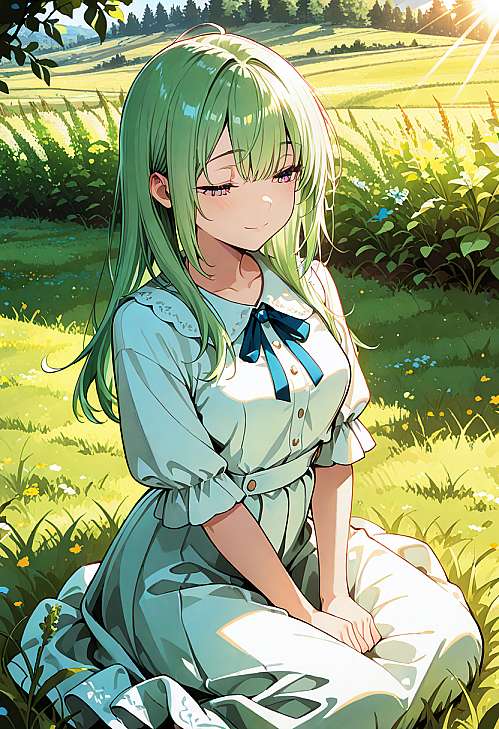我爹算出家里有火劫,想拿我和娘祭天,替他挡灾。当晚,
我就在他床头挂了个断头的纸扎人偶。阿爹,这替身就能替你去死,你也不用烧死娘了。
我爹吓尿了,再也不敢提祭天挡灾的事。却在外头偷偷养了私生子,想让他顶替我执掌家业。
被我诱导去了乱葬岗,吓疯后送进庙里当了和尚。我爹发疯要跟我同归于尽,失手打翻烛火,
死在了大火里。我这桩桩件件让京城里的人个个闻风丧胆。说无人敢娶我这个天煞孤星进门。
我却嫁给了京城里原本籍籍无名的禁军统领李玄凌。相互利用三年,
李玄凌也同当年我爹一般,带回来个怀有身孕的女子。倒是没说要纳妾,
只是说她是天赐的祥瑞,能破我的孤煞命格。在我办庆功宴时,她穿上前朝死人的红衣,
突然发疯见红,冤枉我下咒害她落胎。我理了理袖口的香灰,笑意不达眼底。
找大夫来瞧瞧疯没疯,没疯,就穿着这身晦气衣裳跳到疯为止好了。1苏四妹瘫软在地,
双手护紧小腹。满座宾客皆避之不及,她哆嗦着唇,视线寻不到半个活人。
鎏金护甲拨开她颊边乱发。指尖触感冰凉。你今日,必见血光。声音极轻,
却足以扎进在场每个人耳中。苏四妹身形巨颤,泪水夺眶。夫人,这是李家的祥瑞,
是天意……她哭得凄婉,企图用那块肉博取一丝怜悯。满座权贵唯明家马首是瞻,
无人敢应。我慢条斯理擦拭护甲。明家相术百年,从未出错。李玄凌能有今日,
全凭我一语指点。我的判词,无人能改。一旁的长公主萧锦棠轻笑,指尖把玩酒盏。
命薄之人,承不起泼天恩德。讥讽未落,我抬颚示意。侍女捧上乌木托盘,
盘中叠着那一袭红得刺眼的鸾凤吉服。陈旧檀香混杂异样甜腻,弥散开来。苏四妹瞳孔骤缩。
不……这是……前朝哀后的殉葬服!精神那根弦彻底崩断。李玄凌曾信誓旦旦,
只信我一人。转眼便领回这个试图撼动命盘的变数。既要看人定胜天,
我便让他看这出天命难违。玄凌!救我!李玄凌!苏四妹撕心裂肺,
向着那人不在此处的虚空求救。茶盏重重磕在桌案。啪的一声,满堂死寂。
哭喊卡在喉咙,只余绝望抽噎。红衣掷于她面前,丝绸如一滩化不开的浓血。穿上。
语调不带一丝温度。不是祥瑞么?既是天赐福气,便穿上受着。便是疯了,
也得穿着这道催命符。苏四妹颤抖伸手,指尖刚触及那冰凉料子,便如遭雷击般缩回。
眼中惧意滔天,好似那衣袖中伸出了无数惨白鬼手。想穿不敢穿,她在地上扭曲挣扎,
丑态毕现。帮她。我不欲再看。婆子上前死死按住苏四妹,粗暴套上红衣。
我吹去茶汤浮沫,抿了一口。可惜。面若桃花,印堂却黑得滴墨。红衣加身。
那诡异甜香彻底入骨。苏四妹猛然瞠目,视线所及,宾客、梁柱顷刻化作森森白骨。
啊——!有鬼!她指着虚空尖叫,疯了般撕扯衣物。一片死寂中,鲜红顺着裙摆渗出,
晕开一朵诡然之花。血光之灾应验。宾客噤若寒蝉,无人敢动,无人敢离。长公主举杯示意,
眸中满是赞叹。国师好手段。不费兵卒,便叫敌人自溃。我冷眼看着翻滚哀嚎的苏四妹,
看着那自以为是的筹码化作污血。她以为凭李玄凌的宠爱,便能抗衡天命。
长公主放下酒杯。待会儿李玄凌回来,你如何交代?我扯动嘴角,露出一抹凉薄。
他亲至,看到的也只会是一个污蔑主母、自行发疯落胎的疯妇。长公主轻叹摇头。
明秋水,你这心真狠。我垂眸看茶中倒影。若不狠,早死在宿命漩涡里。心中有鬼,
自见鬼。2苏四妹被拖下去时,指甲在地砖上刮出刺耳余音。血腥气混着冷掉的檀香,
直冲天灵盖。她以为凭那一丝恩宠,便能撬动明家的百年基业。只有死过一次的人才知晓,
命数二字,重如千钧。我垂眸,饮尽盏中残茶。茶汤凉透,正如这人心。若不狠,
我早在那年雷雨夜,便化作了一缕冤魂。十岁那年,我第一次窥见所谓天道。暴雨如注,
惊雷碾碎了夜的沉寂。书房内,烛火在风中疯癫乱舞。父亲明远山跪在蒲团上,
死死盯着那张算出的命盘。卦象大凶——天火焚身,万劫不复。他怕死。
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珠转动,最终定格在母亲身上。既是死劫,便需替死鬼。发妻的命格最硬,
正好用来填这道不可违逆的深渊。空气中没有茶香,只有浓烈刺鼻的火油味。
一根浸透了桐油的粗麻绳,毒蛇般蜿蜒在地,一头系着书房的柱子,
另一头延伸向母亲的卧房。母亲死死捂住我的嘴,将我护在身后。她看懂了丈夫眼底的疯狂。
那不是人眼,是恶鬼索命的红光。秋水,别怕。她声音抖得厉害,指尖冰凉刺骨,
却还是想用那单薄身躯,为我筑一道墙。她想好了,用自己的命,换那疯子一丝良知,
博我一条生路。我没哭。反手扯住母亲濡湿的衣袖,指尖用力到发白。娘,我有法子。
我仰起头,声音轻得像窗外的雨丝。既然天要收人,那便顺应天道。母亲身形骤僵。
她低下头,在那双原本属于孩童的眼里,只看到了一片死寂的深潭。没有恐惧,只有算计。
她读懂了我的未尽之言。颤抖的手缓缓垂下,最终化作一声无声的默许。子夜,雷声更甚。
轰隆巨响掩盖了所有罪恶的脚步声。我赤足踩在冰凉木板上,手中提着一只刚扎好的纸人。
那纸人断了头,身躯空荡,在阴风中飘摇。推开书房门。明远山睡在软榻上,
梦中仍在此起彼伏地惊叫,双手在虚空中乱抓,试图驱赶那些并不存在的业火。我踮起脚,
将那断头纸人悬于床头正上方。惨白的纸躯随风晃动,那一截断颈,正对着他的脸。爹爹。
我甜甜唤了一声。声音软糯,在阴森雷雨夜里,透着诡异的乖巧。女儿为您做了替身,
今夜它替您挡灾。明远山猛然惊醒。他睁眼,正对上那晃动的断头死影。那一瞬,
梦境与现实重叠。预言里的厉鬼具象化,成了索命的修罗。啊——!!!
凄厉惨叫撕破喉咙。滚开!妖孽!滚开!极度惊恐下,他面容扭曲如蜡融,
双手疯了般挥舞。袖摆狠狠扫过案台。哐当一声,烛台倾覆。火苗触及地上的火油麻绳。
轰——火舌瞬间暴涨,如饿兽出笼,一口吞噬了那具颤抖的躯体。烈焰腾空,
映红了半边窗纸。他在火海中翻滚、抓挠,皮肉焦糊味瞬间盖过了火油香。他没有喊救命。
至死,他都在嘶吼那句让他疯魔的判词:预言成真了!预言成真了!我站在门外阴影里,
冷眼看着那团人形火球。火光映在眼底,却没有温度。心有鬼,自见鬼。天火焚身,
确实避无可避。3盏茶凉透。恰如那颗十岁便已坏死的心。若非心死,我活不到今日。
那年夏夜雷雨,惊醒梦魇的并非天威,而是后院铁锤撞击木楔的闷响。一下,又一下。
钝器入肉般,钉进湿潮的夜色。披衣起身,循声至后院。五名家丁正抬着厚重柏木板,
将母亲卧房窗棂死死封堵。神情麻木,动作机械,他们在封一座活人的坟。我不曾出声惊扰。
静立雨中,直至最后一块木板抬起。张三,令郎五岁,命中忌水。声音极轻,
却穿透雨幕。为首家丁脊背骤僵,铁锤险些脱手。李四,高堂咳喘半载,熬不过今秋霜降。
王五……每点一人名讳,便揭一道家中隐秘疮疤。是相术,更是诛心。动作戛然而止。
五张惊恐面孔回转,视我如见恶鬼罗刹。大小姐……谁的主意?语调平直,
不起波澜。无人敢应。指尖拂过那钉了一半的粗糙木板,木刺扎手。父亲让你们做的。
他说明家有天火之劫,需至亲命格去填。母亲命硬,便成了那只好用的祭品。
家丁面色惨白,冷汗混着雨水滚落额角。这是老爷死令,小的们……我知道。
截断他未尽的辩解。明远山想做国师想疯了,他怕死,怕那把火断了他青云路。
今日你们钉死我娘,明日,这长钉会不会钉在你们身上?死寂。唯余暴雨冲刷瓦砾之声。
我抬眼,视线寸寸剐过那些煞白面皮。天道好轮回。谁落下这最后一锤,回禄之灾,
今夜便降临谁家。稚子、高堂、新妇……谁都逃不掉。金石坠地之声骤响。
铁锤滚落泥水。五条汉子连滚带爬四散而去,好似身后有厉鬼索命。明远山很快到了。
裹挟着一身湿重酒气与杀意,双目赤红。他看到了那扇未封死的窗,看到了窗下的我。
眼底无父爱,唯有阴谋败露的惊惶暴怒。逆女!竟敢泄露天机!
枯瘦手掌死死钳住我手腕,力道几乎捏碎腕骨。身体被拖行至早已备好的暖阁。门扉紧闭,
浓烈刺鼻的火油味瞬间封喉。满地泼油,墙角堆柴。这哪里是暖阁,分明是一口精致棺椁。
身体被重重掼在青砖地,膝盖剧痛。正对祖师爷画像。孽障!坏我大事!
今日便用你的命祭天!撑地起身,冷眼对视。在你眼中,我非骨肉。
不过是一道避劫的符纸。笑声溢出喉咙,凄厉刺耳。反手一扯,高悬画像轰然坠落。
抬脚,狠狠以此履碾压神佛面目。若真有神佛,怎会眼盲至此。逆女!
明远山理智全线崩塌。祭祀红绸猛然勒紧我脖颈。空气瞬间被阻隔。眼前阵阵发黑,
肺叶最后一点气息被抽干。我不挣扎。透过他扭曲五官,
视线死死定格在他身后那盏摇曳烛台。三。张口,无声吐字。力道微松,他动作一滞。
二。眼中无惧,唯有一潭死寂,我在宣读他的死期。他浑身剧颤,
眼底癫狂被原始恐惧取代。身后如有不可名状之物。一。字音落下。他如触红烙铁,
猛然松手后撤。惊惶失措的手臂向后挥舞,正如卦象所指——袖摆撞翻烛台。
轰——火舌得势,顺着火油如赤蛇暴起,瞬间吞噬那具颤抖躯体。烈火焚身。
我捂住剧痛脖颈,咳得肺腑生疼。趁火势未成燎原,身躯贴地,爬向墙角那处不起眼的狗洞。
那是早为自己留好的生路。钻出狗洞,复又折返。将早已昏迷的母亲拖出泥泞。身后,
人间炼狱已成。火光冲天,他在喊救命。可卦象说了。今日,他必死无疑。4冬日莲池,
残荷败落,枯梗折在冰面。一声闷响炸开死寂。苏四妹坠入寒潭。冰冷池水灌入口鼻,
她在水中扑腾,搅碎一池枯寂。李玄凌未有半分犹豫。纵身跃入刺骨池水。动作急切,
带着失而复得的惊惶。水珠顺着他紧绷下颌滚落,滴在地砖上,洇开深色水痕。
他解下身上紫蟒袍,死死裹住瑟瑟发抖的苏四妹。那是紫蟒袍。是他初次出征前,
我耗尽心血,在暗纹下绣入挡煞符文的战袍。曾挡流矢,今护灾星。我立于岸边。
看着他满眼怜惜,将那引祸的女子护在心口。寒意顺着脚底攀升,胜过这凛冽冬池。
他抱起人,转身欲回暖阁。我移步,挡在回廊正中。湿邪入体,进门便是家破。
语调平直,却如一道无形屏障,逼停他脚步。气氛凝滞。苏四妹往他怀里缩了缩,牙齿打颤,
语带哭腔。夫君……水底有人拉我脚踝……黑影……是婴孩的手……
她揪紧李玄凌湿透的衣襟,惊恐眼神越过他肩膀,直直刺向我。言语如刃,刀刀指向人心。
李玄凌目光随之刺过来。昔日敬畏依赖,此刻尽数化作憎恶。他信了。信我容不下人,
信我动了阴私邪术。明秋水。他咬牙切齿,你就这般容不下她?我指尖捻过袖口。
一枚早已备好的黄符静躺掌心。既见污秽,我为她驱邪便是。抬步上前。不要!
苏四妹尖叫,指甲掐进李玄凌手臂软肉。不要!我怕!她聪明绝顶。知晓一旦让我近身,
画皮难遮,伪装必破。李玄凌果然将人箍得更紧。看我的眼神,如看择人而噬的妖魔。
让开。我纹丝未动。指尖滑出一枚老旧竹签。那是初见时为他卜的第一卦,
也是他讨去的第一件信物。竹尖直指他眉心命宫。那里曾死气缠绕,是我亲手为他破局。
李玄凌,你当真要为个妖孽,破了满府气运,断了自身生路?他回视。
眼底愤怒化作一丝疲惫哀求。秋水,算我求你。就一次,让一步。我也看着他。
看着那个将脸埋在他胸口、嘴角却微微勾起的女人。今日你若抱她迈过这道门。
我字句清晰。夫妻缘尽。这一句,触了他逆鳞。他最恨被所谓宿命要挟。眼底哀求熄灭,
只剩决绝狠戾。那便尽了!猛然挥手推搡。力道极大。我踉跄后退,
脊背重重撞上假山锐角。痛意钻心。掌心下意识撑地,碎石划破皮肉,鲜血涌出。血珠滴落,
染红了那枚掉落在地的竹签。李玄凌视线触及那抹猩红,有过一瞬凝滞。随即,抬脚。
那只曾踏上青云路的官靴,狠狠碾了下去。咔嚓。清脆断裂声。竹签应声而碎。
他居高临下,声冷如冰。这是教训。别再妄图操控我。言罢,他抱紧怀中人,大步离去,
再未回头。独留我一人立于寒风。低头看掌心血痕。看那被碾进泥泞的断签。我曾用这双手,
为他逆天改命。如今。是他亲手碎了这最后的护身符。5掌心血迹凝固,碎石嵌入皮肉。
看着那截被碾入泥泞的断签,耳畔回荡李玄凌那句“教训”。撑地起身。脊背刺痛蔓延,
远不及心口那片荒原寒凉。逆天改命,换来碎骨扬灰。也罢。拂去掌心泥土,
对候在一旁的红梅道:备车,入宫。红梅惊愕,视线落在我的手掌,欲言又止。
不必包扎。留着这点痛,才好时时清醒。青帷马车行得极稳。闭目端坐,
指腹摩挲袖中那枚龟甲。触感冰凉,正好压下心头翻涌的最后一丝不甘。李玄凌,
既是你亲手斩断生路。那我便不再为你铺路。宫门前,遇见赵无极。如今的司礼监掌印,
御前红人。当年不过是父亲座下因心术不正被逐出的弃徒。面白无须,那张脸上堆着假笑,
眼神淬毒。明大家,稀客。圣上清修,怕是不便。递上拜帖,神色平淡。
有劳公公通传,秋水有要事求见。他接过拜帖,指尖刻意扫过我手背,
目光在那未包扎的伤口停驻一瞬,笑意更深。既如此,明大家稍候。转身入殿,
迟迟未有回音。凛冽寒风穿廊而过。宫人目不斜视,仿佛我只是一尊没有知觉的石像。
暮色四合,宫灯一盏盏亮起。光晕染了飞檐,照不进眼底。终于,殿内传来一声拉长的宣召。
宣,明氏秋水觐见——整衣冠,敛去所有情绪。步入那片吞噬一切的辉煌与黑暗。
金砖冰冷,寒气顺着膝盖钻入骨缝。跪地,叩首。臣妇明秋水,叩见陛下。
御座隐于重重帷幔,只余一道模糊轮廓。慵懒男声从阴影透出。平身。谢陛下。
直身,未敢抬头。臣妇今日入宫,有一事相求。臣妇才疏学浅,恐难堪大任,
恳请陛下收回恩典,准许臣妇与夫君归隐田园。殿内死寂。唯有机括转动的轻微声响,
一下下敲击耳膜。良久,御座传来一声轻笑,满含讽刺。李玄凌正值盛年,前途无量。
你身为贤内助,怎可轻言退隐?语调微顿,带了几分玩味。还是说,你看出了什么,
想提前抽身?垂眸。臣妇愚钝。呵。一只手拨开帷幔。余光瞥见御座旁小几上,
赫然摆着父亲当年遗物——紫檀星盘。皇帝手指正按在星盘某处。指尖之下,
是用朱砂重重圈出的两个字。七杀。那是我的命格。彻骨寒意从尾椎蹿升,
瞬间冻结四肢百骸。终于明白。他留我,非为牵制李玄凌。李玄凌的荣宠,甚至明家相术,
皆是陪衬。他真正想要的,是我这七杀的命。要用这至煞至凶的命格,
为这病入膏肓的王朝,挡那倾天之灾。以我为祭。俯身,额头重重贴上冰冷金砖。
陛下圣明,是臣妇糊涂。语调平稳,听不出半分异样。臣妇,遵旨。
御座之人似乎满意我的顺从,挥手。退下吧。依言退出大殿。每一步沉稳如初。
直至殿门缓缓合上,隔绝那道洞穿人心的目光,后背早已冷汗浸透。红梅快步迎上,
扶住我手臂。夫人,回府吗?回府?回那个已无我立锥之地、只剩断壁残垣的牢笼?
望向远处宫墙上空。一弯冷月如钩,割开浓稠夜色。既然天子不肯放我生路。
那我便换个天子来求。收回目光,冷冷吐字。去长公主府。6马车停稳。朱门紧闭,
两盏硕大灯笼在寒风中剧烈摇曳,如两只泣血鬼眼。无需通传,径直踏入。穿过回廊,
水榭内暖香扑鼻,靡靡之音穿透窗棂。那是腐烂的甜腻味道。长公主萧锦棠倚在软榻,
薄纱宫装半敞,大片雪白肌肤暴露在空气中。三五名面首跪伏于侧。有人抚琴,
有人剥去葡萄皮,将晶莹果肉喂入那张朱唇。好一派醉生梦死。挥退引路侍女,步入水榭。
琴声戛然而止。面首们动作僵滞,神色惊惶,视线不安地游移。萧锦棠抬眼,醉意朦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