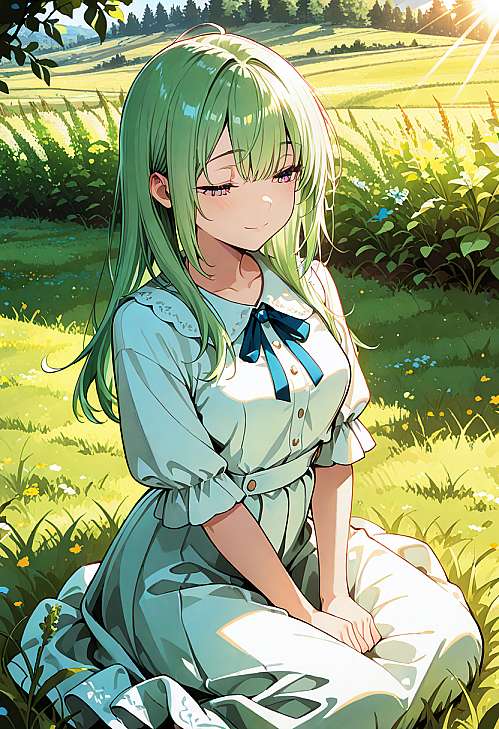导语我是话本子里“恶毒女配”。站在太液池边,说着我命由我不由天。不是被废去封号,
在皇陵孤寂疯癫,就是“突发急症”,然后悄无声息地“暴病而亡”。身体失重,
冰冷的湖水从四面八方涌来,瞬间吞噬了所有喧嚣与视线。
只有水面上破碎的、晃动的琉璃瓦金光,刺得人眼睛发痛。“这结局……”“我自己选。
”01三年后。京城西市的晨雾,混着尘土和炊烟。沉重的石磨转动声“隆隆”作响,
豆腥气浓得化不开,丝丝缕缕钻进鼻腔。我系着粗布围裙,将泡发的豆子一瓢瓢舀进磨眼。
直到急促的马蹄声,混着甲胄特有的金属摩擦音,由远及近,粗暴地撕开市井的喧嚷。
一辆玄黑马车,在玄甲骑兵的簇拥下,碾过青石板路,稳稳停在了我的豆腐摊前。帘幔未动。
一道沉冷的目光,却仿佛穿透车壁,死死钉在了我正握着瓢、沾满豆沫的手上。
摊子前瞬间一静。几个等着买豆腐的老主顾,缩着脖子往旁边挪了挪,
眼神惊疑不定地瞟向那队煞气腾腾的骑兵。我低头,继续舀豆。磨盘“吱呀”转动,
乳白的浆液顺着石槽汩汩流出,落入桶中。
马车帘子终于被一只骨节分明、带着旧疤的手掀开。陆砚行下了车。他一身墨色常服,
腰佩长剑,身姿依旧挺拔如松,只是眉宇间凝着化不开的阴郁,下颌线绷得死紧。
三年边关风沙,在他脸上刻下了更深的痕迹。他一步步走过来。摊子前彻底没了旁人。
我在围裙上擦了擦手,抬起眼皮。“军爷,买豆腐?”声音平直,
带着西市妇人特有的、略显粗嘎的调子,“今日的卤水老豆腐,压得实,煎炒炖煮都好。
要不来两块?”陆砚行没说话。他的目光从我沾了豆渣的鬓角,扫到洗得发白的粗布袖口,
最后定格在我低垂的、刻意避开视线的脸上。然后,他伸出手。不是递钱,
是径直朝我的下颌而来。我猛地后退半步,
同时双手端起案板上刚成型、还裹着湿布的一大板豆腐,稳稳横在两人之间。“军爷,
”我抬高了点声音,透着股市井的泼辣与小心,“豆腐娇嫩,碰不得。您要是手重了,
这一板子可就算您的了,五十文,不还价。”陆砚行的手僵在半空。
他的瞳孔细微地收缩了一下,视线落在那板白白嫩嫩、微微颤动的豆腐上,又移回我的脸。
那双眼睛里,此刻翻涌着极其复杂的东西,震惊、怀疑、一丝不易察觉的痛楚,
更多的是深不见底的探究。“你……”他的喉咙像是被砂石磨过,挤出干涩的音节。
我没给他问出口的机会。侧身,将豆腐板放回原位,动作麻利地切下一角,用油纸包好,
递过去。“尝尝?不好吃不要钱。”我扯出个做生意式的笑脸,“民妇阿灼,
在这西市卖了两年豆腐,童叟无欺。”陆砚行没接那包豆腐。他只是死死盯着我,
仿佛要将我这身粗布衣衫和这张平庸寡淡的脸皮生生剐下来,看看底下到底藏着什么。半晌。
他猛地转身,走回马车。“走。”玄甲骑兵如来时一般,沉默地簇拥着马车离去,
留下一地压抑的尘土。旁边卖菜的大娘这才哆哆嗦嗦凑过来,拍着胸口:“哎哟我的娘嘞,
阿灼,你、你啥时候惹上这等煞神了?那是北边回来的将军吧?”我重新握住石磨的木柄,
用力推转。“谁知道呢。”我扯了扯嘴角,看着豆浆流淌,“许是……认错人了吧。
”磨盘“隆隆”作响。盖过了我胸腔里,那擂鼓般的心跳。02陆砚行没走远。或者说,
他的人没走远。豆腐摊斜对面的茶肆二楼,临窗的位置,终日坐着两个便装汉子,眼神锐利,
目光时不时就扫过来,钉子一样。收摊时,我刚把厚重的木锅盖盖上炉子,
其中一个汉子就大步走过来。“娘子,我们将军吩咐了,”他语气硬邦邦,“这摊子重,
以后早晚收摊,我们哥俩帮您搬。”不是商量,是告知。我擦汗的手顿了顿。“军爷好意,
心领了。”我低头收拾碗勺,“小本生意,雇不起帮手。我自己来就行。”那汉子像没听见,
直接上手去抬炉子。我抢先一步按住炉沿。“军爷,”我抬起眼,直视他,
“西市有西市的规矩。无故添人帮手,市吏要查,左右摊位要说道。我一个寡妇,
担不起闲话。”寡妇。这两个字吐出来,汉子的动作僵了一下,
脸上闪过一丝极不自然的情绪。他嘴唇动了动,没再坚持,退开两步,却也没走远,
抱着胳膊站在巷子口。推着堆满家什的板车回到租住的小院,栓上门,我才靠着冰冷的门板,
缓缓吐出一口一直憋着的气。掌心一片湿冷。不是汗。是后怕。院子里,
我收养的流浪儿小宝正蹲在地上看蚂蚁,黑葡萄似的眼睛望过来:“阿娘,今天有坏人吗?
”我走过去,摸摸他的头发。“没有。”我说,“是阿娘看错了。”夜里,我睡不着。
起身坐在窗前,就着惨淡的月光,慢慢磨着一把切豆腐的薄刀。磨刀石发出“沙沙”的轻响,
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。窗外,隐约能看到那两人轮换守夜的身影,印在窗纸上,一动不动。
我看着那影子,手里的动作没停。刀刃渐渐泛出冰冷的微光。恍惚间,
这月光好像变成了许多年前,东宫暖阁里明亮的宫灯光晕。少年将军陆砚行跪在殿中,
当着父皇和太子哥哥的面,割下一缕头发,双手奉上。他的声音清朗坚定,
掷地有声:“臣陆砚行,在此立誓。”“此生此身,刀锋永为公主所指,忠心永不蒙尘。
”“如违此誓,天人共戮,死无葬身之地!”那时,我坐在珠帘后,心跳得快极了,
脸颊发热,觉得这世上再没有比这更好听的誓言。后来呢?后来,
在我被“请”去皇陵“静养”的那天,也是他,带着禁军,亲自“护送”。宫道那么长,
长到我以为走不到头。我抓着他的甲胄,指尖掐得发白,哭着问他:“陆砚行,你的誓言呢?
你说过你的刀……”他别开了脸,侧脸线条冷硬如铁。“公主,
”他的声音低得只有我能听见,却像冰锥刺进心里,“臣的刀,现在要护卫大梁的江山安稳,
和……未来的太子妃。”“请您,体面些。”体面。我松开了手。磨刀声停了。我举起刀,
对着月光看了看锋刃。又低头,看了看水缸里模糊的倒影。粗布钗裙,面色憔悴,
一双手因为常年泡水劳作,粗糙红肿,指节微微变形。哪里还有半分永宁公主的影子?
“也好。”我对着水中的影子,极轻地笑了笑,声音散在夜风里。
“萧灼华已经死在太液池了。”“现在活着的,是阿灼。”03陆砚行的人守了五天。
第六天早上,他们忽然撤走了。茶楼窗口空了,巷子口也没了那两尊“门神”。我照常出摊,
心里却没松快多少。暴风雨前的平静,往往更让人窒息。果然,午市刚过,
摊前人少了些的时候,另一辆不起眼的青篷马车,停在了街对面。车帘掀开,下来一个人。
一身半旧的天青色儒衫,身形清瘦了许多,脸色是一种不健康的苍白,眼下带着浓重的青黑。
他站在那里,看着我的豆腐摊,看了很久很久。他才慢慢走过来。脚步有些虚浮,
全然不似以往的沉稳雍容。我的太子哥哥,萧允之。他停在我的摊子前,
目光从我沾着豆渍的围裙,看到我正在滤浆的、布满青筋和老茧的手,
最后落在我低垂的、刻意用头巾遮挡了半边的脸上。他的嘴唇开始不受控制地哆嗦。
眼眶几乎是瞬间就红了。“灼……”他开口,声音哑得厉害,第一个音节就破碎不堪。
我放下滤布,在围裙上擦了擦手,恭敬地、带着恰到好处的疏离和疑惑,微微屈膝。
“这位……公子,您要买豆腐?嫩豆腐还是老豆腐?
”萧允之像是被我这声“公子”和这副全然陌生的做派狠狠刺了一下,猛地后退了半步。
“灼华……”他终于挤出了完整的词句,带着浓重的鼻音和哭腔,
“你的手……你怎么……怎么能做这些粗活……”他伸出手,似乎想抓住我的手查看。
我迅速将手背到身后,又后退一步,拉开了距离。“公子定是认错人了。”我垂着眼,
语气平板,“民妇姓林,夫君早亡,街坊都唤我一声阿灼。不做这些粗活,我和孩子吃什么?
”“夫君……早亡?”萧允之重复着这四个字,脸上的血色“唰”一下褪得干干净净,
连嘴唇都失了颜色。他摇晃了一下,仿佛站不稳。“你……你嫁人了?还有了……孩子?
”每一个字,都像是从他喉咙里抠出来的,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骇和……痛楚。“是。
”我抬起头,坦然迎上他崩溃的目光,“亡夫是走货的商人,命不好,遇了山匪。
留下我们孤儿寡母,总要活下去。”我指了指旁边正在帮我搬豆袋的小宝。小宝很机灵,
立刻跑过来,躲到我身后,怯生生地看着这个陌生的、表情可怕的“贵人”。
萧允之的目光移到小宝身上,那眼神空洞得吓人,像是某种信仰骤然崩塌。
“活下去……”他喃喃道,眼泪毫无征兆地滚落下来,“你就这样……这样活下去的?,
”我没接话,转身继续去滤豆浆。木架上的棉布沉甸甸的,我需要用力抖动,
才能让浆水流得更快。豆渣溅起来,几点落在我的手背上,我也没擦。萧允之就站在那里,
一动不动地看着我劳作,看着我用那双他曾牵过的手,熟练地干着最脏最累的活计。
他的眼泪流个不停,无声无息,却比嚎啕大哭更让人窒息。不知过了多久,
隔壁卖炊饼的大婶领着自家小孙子过来,递上一文钱:“阿灼,来块嫩豆腐,
小崽子吵着要吃你做的豆腐脑。”我应了一声,麻利地切豆腐,浇上备好的卤汁,
撒上葱花虾皮,笑盈盈地递过去:“小心烫。”那笑容,热情,卑微,讨好,
是市井妇人最寻常不过的样子。萧允之看着我对旁人展露的笑脸,
看着那孩子捧着碗吃得香甜,看着小宝也凑过去眼巴巴地瞧,
大婶顺手也给他喂了一口……他忽然踉跄着转过身,像是再也无法忍受,
逃也似的朝马车走去。走了几步,他又在巷子口停住,回头望来。我正蹲下身,
用袖子给小宝擦嘴角的卤汁,侧脸柔和,眼神平静。那画面,温馨,寻常,
却与他记忆里那个骄纵明艳、只会对他撒娇耍赖的妹妹,隔着山海,隔着生死。
他最终什么也没说,钻进了马车。马车缓缓驶离西市,消失在尘土和喧嚣里。
我脸上的笑容一点点淡去,直至冰冷。我摸了摸小宝的头。“没事了。”我说。
不知道是在安慰他,还是在告诉自己。04平静了没两天。夜市刚支开摊子,灯火初上,
人流渐密。我正在给客人切一块干豆腐,余光瞥见一道青衫身影,
安静地立在摊位斜对面的灯笼阴影下,不知看了多久。谢清让。东宫侍读,曾经的寒门才子,
得我举荐,才得以在太子哥哥面前展露头角。也是最后关头,
亲手拿走父皇留给我唯一生路的人。我手下的刀没停,利落地将豆腐切好,包上油纸,
递给客人,收钱,找零,一气呵成。“娘子,生意不错。”温润的声音在摊前响起。
谢清让走了过来。他比三年前清减了,气质依旧儒雅,
只是眼底深处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与……阴郁。“谢大人。”我微微颔首,
语气平淡如对待任何一位可能光顾的官人,“您也来逛夜市?今日有现炸的豆腐丸子。
”谢清让没看豆腐,目光落在我洗得发白的头巾上,又扫过摊子简陋的摆设。“故人相见,
娘子就只谈生意吗?”他声音压得很低。“民妇与大人,似乎并非故交。”我拿起抹布,
擦拭着案板上的水渍。谢清让沉默片刻,忽然从袖中滑出一物,置于案板一角。
那是一支玉簪。质地算不得顶好,样式也简单,簪头是一朵小小的、半开的玉兰花。
是我及笄那年,自己画了样子,命宫外玉匠随意打的。戴过两次,后来不知丢到哪里去了。
“物归原主。”谢清让的声音更低了,几乎淹没在周围的嘈杂里。我看着那支玉簪,
泛着温润却陈旧的光。指尖几不可察地蜷缩了一下。然后,我伸手,
用抹布将那玉簪往他那边推了推。“大人说笑了。”我抬起眼,目光平静无波,
“这么好的玉,民妇可戴不起,也配不起。我发间这支桃木簪,三两文钱,顶合适。
”谢清让的呼吸滞了一瞬。他看着我发间那根粗糙的、毫无雕饰的桃木簪子,眼神复杂难辨。
“三年前……”他开口,声音艰涩,“臣……有负所托。”有负所托。好轻巧的四个字。
我差点笑出声。“谢大人言重了。”我重新拿起刀,开始切下一块豆腐,
“您如今是天子近臣,前程似锦。过去种种,于您而言,不过是微尘罢了。”我顿了顿,
刀锋停住,抬眼看他,目光里是彻底的疏离和一丝冰冷的讥诮。“就像这磨出来的豆浆,
泼出去了,难道还能一滴不漏地收回来吗?”谢清让脸色白了一分。他张了张嘴,
似乎想辩解什么,最终却只是将那支玉簪紧紧攥回掌心,指节捏得发白。
“殿下……”他换了称呼,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恳切,“西市鱼龙混杂,并非久居之地。
您若愿意,臣可以……”“民妇阿灼,在此谢过大人好意。”我打断他,语气斩钉截铁,
“我在此处营生,养家糊口,心安理得。不劳大人费心。”这时,又有客人过来。
谢清让深深看了我一眼,那眼神里有愧疚,有挣扎,还有些更深、更暗的东西,我看不分明,
也不想分辨。他终是没再说什么,转身没入熙攘的人流。我继续招呼客人,切豆腐,收钱,
笑容无懈可击。直到收摊,推着板车往回走。夜风吹在脸上,凉飕飕的。
我摸了摸发间的桃木簪。粗糙,廉价,却让我觉得踏实。泼出去的豆浆,确实收不回来。
就像死过一回的人,再也变不回从前。05三人来过之后,西市的气氛变得微妙起来。
先是管这片街区的市吏,巡查得格外勤快。经过我摊子前时,目光总要多停留几秒。接着,
左右摊位的大婶大娘,看我的眼神也多了几分探究和疏离。“阿灼啊,
”卖菜的张婶趁着人少,凑过来小声嘀咕,“你……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?我听说,
上头好像在查什么‘犯官家眷’流落市井的事儿……”我心里一沉,
面上却不解:“婶子说笑了,我一个寡妇,带着孩子卖豆腐,能得罪谁?查就查呗,
身正不怕影子斜。”话虽如此,我却知道,平静的日子,到头了。深夜,小宝睡着后。
我点亮油灯,从床底最深处,摸出一个巴掌大的、裹了好几层油布的小包。层层打开。
里面是一枚半个巴掌大的铜制鱼符。样式古朴,入手沉甸甸的,
雕刻的鱼鳞纹路在昏暗灯光下,泛着幽冷的光。父皇驾崩后,公公悄悄派人塞给我的。
鱼符可调动一支隐秘的、行走于西域和江南的皇家商队。这大概是他老人家,
在察觉风雨将至时,为我这个注定“命不好”的女儿,留下的最后一条生路,
和一份足以安度余生的财富。可惜,我还没来得及用上,就“死”了。
而商队的信息和那笔钱……想必早已成了萧婉柔嫁妆单上最耀眼的一笔。
我将鱼符紧紧攥在掌心,冰凉坚硬的触感,提醒着我曾经拥有过什么,又失去了什么。走吗?
再次像三年前一样,抛下刚刚熟悉的一切,隐姓埋名,逃往未知之地?
我看着床上小宝熟睡的脸,又环顾这间虽然简陋、却一点点布置出“家”的样子的租屋。
灶台是冷的,但明天一早生起火,就会有豆浆的香味。磨盘是旧的,但转起来的声音,
让人心安。我逃过一次了。难道要逃一辈子?门外,似乎有极轻微的脚步声掠过,很快消失。
是监视?还是仅仅路过的打更人?我吹熄了灯,坐在黑暗里。心脏在寂静中,
缓慢而沉重地跳动着。06我没能立刻逃走。因为一桩“生意”,找上了门。
东宫要为即将举行的京郊围猎大宴采买些新奇吃食,不知怎的,
我那点仿制御膳样式做的豆制点心,竟入了采办太监的眼。点名要“林氏豆腐坊”出人,
随队前往围场,专司供应部分豆品菜肴。皇命难违,市吏亲自来“请”,容不得我拒绝。
我只好将小宝托付给隔壁还算信得过的张婶照看几日,
自己带着两个帮工实则是陆砚行留下的、换了装束的亲兵,拉着一车豆料和工具,
跟着采办的队伍,去了京郊皇家围场。围场依山傍水,旌旗招展,帐幕连绵。
空气中弥漫着皮革、马匹和草木的气息,混合着一种无形的、属于皇室与权力的威压。
我被安置在供应区边缘一个简陋的帐篷里,远离核心的华丽营帐。这样也好。我低着头,
指挥帮工搭起临时灶台,浸泡豆子,准备明日宴会要用的各色豆糕、豆腐。热闹是贵人们的,
与我无关。我只想快点做完差事,拿到那份不算丰厚的赏钱,然后回到我的西市小摊。
第二天,围猎开始。号角长鸣,马蹄声如雷震动大地,呼喝声、猎犬吠叫声远远传来。
供应区相对安静,只有各色仆役厨娘穿梭忙碌。我正在滤最后一批豆浆,准备点卤。突然!
外围传来一阵惊恐的尖叫和骚乱!“鹿!冲过来了!”“快躲开!”我猛地抬头,
只见远处山林边缘,烟尘滚滚,几十头体型健壮的鹿,它们显然受了极大的惊吓,横冲直撞,
踢翻了好几个临时搭建的灶台和货架!人群瞬间大乱,
哭喊声、躲避声、东西倒塌声混成一片。供应区多是妇孺和文弱仆役,哪里见过这种阵仗,
顿时像没头苍蝇一样乱窜。“小宝——”我脑中瞬间一片空白,竟忘了小宝不在身边,
下意识就要往人堆里冲,想去找他。就在此时,一头格外高大的公鹿,低着头,
尖锐的鹿角对准人群最密集的方向,狂奔而来!它所过之处,桌翻架倒,汤汁四溅!
而那个方向,恰好有几个吓得呆住、蹲在地上哭泣的小宫女!我来不及多想,
抓起手边一个厚重的空木桶,用尽全身力气,朝那公鹿冲来的方向侧面砸了过去!“砰!
”木桶砸在公鹿侧腹,让它痛呼一声,冲势微微一偏。但也仅仅是一偏。它甩头,
赤红的眼睛竟转向了我!后蹄蹬地,再次加速冲来!距离太近,
我甚至能闻到它喷出的腥热气息,看到它鹿角上沾着的草屑泥土!躲不开了!
电光石火间——“唏律律——!”激烈的马嘶声几乎刺破耳膜!一道玄黑色的身影,
骑着一匹神骏的黑马,如同闪电般从斜刺里冲出!马速快得惊人,在即将撞上鹿群的瞬间,
马上之人猛地一提缰绳,战马人立而起,碗口大的铁蹄狠狠踏下!同时,
一道雪亮的剑光闪过!“噗嗤!”血光迸现!那匹冲在最前的公鹿惨嚎着倒地,
脖子上赫然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。而另一匹快马也从另一个方向赶到,
马上之人甚至来不及下马,直接飞扑过来,一把将我拽离了原地,因为冲势太急,
两人一起滚倒在地。“灼华!”惊惶到变调的声音,是萧允之。几乎同时,
陆砚行也已斩倒两头鹿,控住马匹,一跃而下,大步冲到我面前,
他的脸色比那公鹿的血还要白上三分。“你怎么样?!”两人异口同声,同时伸出手,
想要抓住我检查。周围,鹿群或被斩杀,或被赶来的侍卫驱散,骚乱渐渐平息。无数道目光,
或明或暗,从四面八方投射过来。有惊愕,有好奇,有探究,有幸灾乐祸。
我推开护着我的萧允之,自己撑着地面,慢慢站了起来。裙摆沾满了泥土草屑,
手臂在刚才被拽倒时擦破了皮,火辣辣地疼。但我只是平静地拍打着身上的尘土,
然后对着眼前两个位高权重、却在此刻显得狼狈不堪的男人,微微屈膝。“民妇无事。
”我的声音不大,甚至有些沙哑,却清晰地在渐渐安静的供应区响起。“谢皇上,
陆将军搭救。”说完,我不再看他们瞬间惨白僵硬的脸色,转身走向我那被撞倒一半的灶台。
豆浆洒了一地,洁白的浆液混入泥土,一片狼藉。我蹲下身,默默收拾。高台之上。
一身华服、被众多宫女内侍簇拥着的皇后萧婉柔,静静地站在那里,
将方才发生的一切尽收眼底。她手中那柄精巧的团扇,几不可察地,停顿了一瞬。美眸之中,
掠过一丝极冷的、幽暗的光。07围场“惊鹿”事件后,我被变相“保护”了起来。或者说,
软禁。供应区的差事被莫名其妙地提前结束,赏钱倒是丰厚地发了下来。
但我没有被允许立刻返回西市,而是被“安排”暂住在围场外围一处僻静简陋的废弃营房里,
理由是“受惊需休养,且需配合查清惊鹿缘由”。我知道,这是萧允之和陆砚行的意思。
他们怕我再“消失”。可这突如其来的“关切”,已经太迟了!不是吗?第三天夜里,
下起了暴雨。狂风卷着豆大的雨点,砸在房顶,发出噼里啪啦的巨响。
雷声在远处山峦间滚动,电光不时撕裂漆黑的夜空。这是我以前最怕的雷声,
以前总有太子哥哥给我讲故事,哄着我入睡,而现在我不怕了,
我甚至觉得这是最好的逃跑机会。直觉告诉我,留在这里,只会更危险。
我悄悄收拾了仅有的几件衣物和那枚鱼符,用油布仔细包好贴身藏好。然后,
我吹熄了屋里唯一一盏昏暗的油灯,静静坐在黑暗里。大约子时过后,风雨声依旧狂躁,
雷声渐歇。门外守卫交接的细微动静传来,片刻的松懈。就是现在!我轻轻推开后窗,
身形灵活地钻了出去,落入冰冷刺骨的雨幕中。泥水瞬间淹没了脚踝。
凭着白天的观察和记忆,我朝着与营区相反的山林方向,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去。
雨水模糊了视线,冰冷的衣服紧紧贴在身上,沉重又束缚。头发黏在脸上,狼狈不堪。
但我不能停。不知道跑了多久,感觉肺都要炸开,终于在山脚下看到了一座废弃的山神庙,
门楣半塌,在风雨中飘摇。我冲进庙里,浑身湿透,冷得牙齿咯咯打颤。庙宇很小,
正中是残破的山神像,积满了灰尘蛛网。地上有凌乱的干草和烧过的灰烬痕迹,
看来偶尔有流浪汉或猎户在此落脚。我找到一个相对干燥的角落,蜷缩起来,
试图汲取一点微不足道的暖意。就在我以为暂时安全了的时候。庙门口的光,
被一个高大漆黑的身影,完全堵住了。他一步步走进来,玄色的衣袍同样湿透,
紧紧贴在身上,雨水顺着他棱角分明的下颌,不断滴落。是陆砚行。他竟然……追来了。
而且,只有他一个人。他停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,没有立刻靠近。庙外惨白的电光一闪而过,
照亮了他苍白的脸和那双死死盯着我的、翻涌着骇人情绪的眼睛。外面的雨声,庙里的寂静,
形成诡异的对峙。“萧、灼、华。”他一字一顿,声音沙哑得如同沙石摩擦,
每一个字都带着雷霆般的怒意和……某种更深沉的东西。“你要躲到什么时候?!
”他猛地向前一步,气势惊人。“你看看你现在!像个什么样子!
”他的目光扫过我湿透褴褛的衣衫,凌乱粘腻的头发,冻得发青的嘴唇,
最后落在我下意识护在身前、沾满泥污的手上。那眼神,像是痛极,又像是恨极。
“跟我回去。”他深吸一口气,似乎努力压抑着翻滚的情绪,但声音依旧紧绷,
“现在局势不同了,我立了军功,我有筹码!我可以向陛下请旨,用我的功劳,
换你重得封号,换你……”“然后呢?”我打断了他,声音因为寒冷和疲惫而微微发抖,
却异常清晰。我抬起头,看着他,雨水顺着我的额发流进眼睛里,涩得发疼。“然后,
再做一次你们献给萧婉柔的、彰显她善良大度和你们情深义重的祭品吗?
”陆砚行像是被狠狠打了一拳,高大的身躯几不可察地晃了一下。“不是……不是祭品!
”他急急反驳,眼中掠过一丝狼狈,“这次不会!我会保护你,我发誓!
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!”“发誓?”我忽然笑了,笑声在空旷破败的庙宇里,
显得格外凄凉讽刺。我慢慢站起身,因为寒冷和脱力,脚步有些虚浮,但我挺直了脊背。
然后,我当着他的面,缓缓卷起了左臂湿透的衣袖。手臂内侧,靠近肘弯的地方,
一道狰狞的、暗红色的疤痕,在昏暗的光线下,如同一条扭曲的蜈蚣,
盘踞在曾经细腻的皮肤上。那是当年在皇陵“静心苑”,一次“意外”失火时,
被掉落的梁木烫伤所留。没有及时得到医治,溃烂了很久,才勉强愈合,
留下了这道丑陋的印记。陆砚行的呼吸,骤然停止了。他的眼睛死死盯住那道疤,
瞳孔剧烈收缩,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,比外面的闪电还要白。“保、护、我?”我一字一顿,
将这三个字,连同手臂上这道永不褪色的耻辱和伤痛,一起砸回他脸上。“陆将军,
您当年皇陵失火,是您自己选择保护的萧婉柔,我当时躺在那里,您明明知道啊,
是你押送我进去的不是吗?”我的声音越来越高,
带着积压了三年、终于破土而出的恨意和尖锐。“你现在说要保护我?拿什么保护?
用你这把,曾经对着我亮出锋刃的剑吗?还是在我受伤时替我将所有太医让给萧婉柔?
”陆砚行脸上的肌肉剧烈地抽搐着,他想说什么,嘴唇颤抖着,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
他只是死死地看着那道疤,仿佛第一次真正看清,他当年的“不得已”和“体面”,
究竟意味着什么。他猛地伸出手,似乎想碰触那道疤痕,指尖却在即将触及的瞬间,
剧烈地颤抖起来,最终颓然垂下。“我……”他喉咙里发出困兽般的嗬嗬声,
“我当时是想救你的,但是萧婉柔是太子妃,我以为…………我以为有人来救你,
我以为……”“你以为?”我猛地甩下袖子,遮住那道疤,也遮住自己瞬间汹涌而上的泪意。
“你以为什么不重要了,陆将军。”我转过身,不再看他,面向着庙外无边的风雨黑夜。